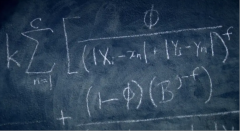我的家乡在大理,凭借低廉的房租,优美的自然风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成为不少人的乌托邦,也是新兴的“数字游民”热衷的目的地。
在返乡之前,我想象了一种大理数字游民的生活,远方的都市人群,来到我的家乡,隐居乡野,看云卷云舒,生活成本低,舒适安逸,但挣得又多,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文化。
龙恩就是其中一员,她出生于2000年,瘦瘦的,瓜子脸上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温温柔柔的模样,但眼神里似乎有一种倔强和坚定。去年,她被上海的一家公司裁员了,带着裁员补偿,不到一万元的全部家当,坐了39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云南。
她说自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但毕业后的全职工作似乎都不是很顺利。在23岁的年纪决定去做自由职业,对她来说是一次脱离轨道的冒险,也有很多无奈的成分。
刚来大理的时候,龙恩是兴奋的。路边一朵野花,天空一抹晚霞,随拍都让她感到惊艳。2023年7月她写道,“大理的日落在8点十几分,外地人来大理,不小心就会被阳光欺骗,本地的小吃店,七点多,天还亮着,老板就关上了红棕色铁门。不像大城市,所有人都在高强度运转。”
今年一月,似乎已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对大理有些厌倦了。傍晚坐高铁回来,下车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枯萎了。我还是喜欢城市生活,喜欢711便利店的南瓜小米包和鸡胸肉便当。喜欢几分钟一班的公交车和地铁。”
大理数字游民社区NCC主理人大曹发现,大理似乎是一个有结界的地方。游客看到的,隐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个大理。她在“流动的筵席”里支了一张桌子,一拨一拨的数字游民,人来人往,筵席仍在。

2月8日,NCC社区所在的葱园村,远处是苍山。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成为数字游民
春节返乡,候鸟迁徙,我从北京回到大理,广东女孩龙恩并没有离开,她住在距离大理古城往北3公里的上鸡邑村。
去年,龙恩从一个编辑那里听说,很多自由撰稿人在大理,生活成本低,自然环境好。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来过云南,但想到这是一种经人验证过的可行的生活方式,于是多了一些勇气。去年5月,她搬到大理,开启了数字游民的生活。
这里公共交通不便,村落一家稻田咖啡馆,是离她最近的定位。沿着咖啡馆对面的巷子往深处走大概50米,左手边一栋灰砖白墙的两层半白族房屋就是龙恩在大理的家。
院落的一楼,房东在堂屋看电视。二楼是龙恩的房间,大概10平米,窗户朝西,可以看见远处的苍山,下午的光照进来,明亮温暖。一张床、一个长约两米的三层白色置物柜、一个木质的鞋架、一张圆形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热水壶、多功能煮锅、洗漱的盆、一些快递盒子放在地面上。但乱中有序,在圆桌上,摆着几本书和电脑,盖了一块印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蕾丝花边桌布,淡紫色的花瓶里插着几支枯萎的玫瑰花。
龙恩就在这个房间里写作。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房租500元一个月,月付。
房东的女儿也住在二楼。龙恩要和其他租客共用客厅和卫生间。厨房则是一个简易的彩钢瓦搭建的棚子,位于一楼院落东侧。
这是一栋完全本土化的房子,外观传统,内部装修简洁,物品摆放也很随意。乍一进门,就像走进某个亲戚家。
从她居住的地方走出去不到10分钟就有一个小型菜市场,售卖着当地村民自己种的新鲜菜品,不过龙恩大多数时候选择美团买菜,等她醒来,临近中午,很多摊贩已经收摊了。她逛过几次,但很少买,她说自己不会挑,在美团上买可以看评价。这是我在北京的买菜方式,而大理的食材新鲜,市场充满了人间烟火,逛菜市有一种闲情。如果我打开某个软件看点评,我的本地同学们会开玩笑说,你好像是个外地人。

龙恩的房东在一楼搭建的简易厨房。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试错的生活
在村里生活,步行就够了。龙恩曾经租赁过一段时间的电瓶车,200块一个月,不贵,但相比她的出门频率来说,并不划算。
在大理的这十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煮面,吃到反胃,她开始尝试买电饭锅和大米,自己炒菜,后来厨艺突飞猛进,学会了番茄炖牛肉,虾仁豆腐煲。她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做饭,因为外卖能送到的很少,可选择的不多。大理的米线饵丝,酸辣也不合她的口味。饮食上,她喜欢粤菜,偶尔吃的西餐、火锅也并不是大理特色。
在北京写稿,在广州写稿,还是在大理写稿,对于龙恩的一个明显区别可能是,田野,湖泊,广阔天地,显得触手可及。沿着乡村小路步行20分钟,她就能来到洱海边,看一朵云,从东边飘到西边,再吹一阵晚风,思绪零落又逐渐平静。但是自然的治愈是短暂的,只有工作状态稳步上升,才能保持更稳定的内核。
生活成本低,提供了更多试错的可能。十个月来,她完成了七篇长稿,还有两篇即将发布,这个产量不算多。去年八九月份,经济一度非常窘迫,龙恩投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篇长稿,但是最终没有找到平台发布,没有稿费。
她只好去寻一些兼职,在4公里开外的古城酒吧、咖啡店做过兼职,两份兼职时间都不长,她挣了不到一千元。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她的心理也出现了抑郁状态,不想起床,不想做饭,白天拉上窗帘,晚上也不开灯,自我封闭,不知道这份自由职业怎么做下去,她打过心理热线,对着电话那头一直哭泣,后来她预约了公益的心理咨询,每周一次。
直到2023年底,龙恩每月能完成两篇长稿,稿费千字500-700元,她的经济稍微好转。她认识了另一位同样是自由撰稿的数字游民,对方给国内一家头部媒体和专业文学杂志供稿,同时也在写书,除了写作,他还尝试做餐饮,每餐收费15-20元。他曾邀请过龙恩一起写作,但因为写作风格和方向的差异,没有深聊下去。
起初,龙恩热忱探索大理的一些文艺活动,比如篝火,观影,脱口秀,都是和她一样的外来城市青年组织的活动,但她觉得,总体内容质量偏低,每每乘兴而去,失望而归。
她也加过数字游民的社群,但群里大家主要邀约的是吃喝玩乐,和她想象的深度精神交流也有差距,她没有融入其中。没有社群支持,离本地人的生活圈子也遥远,写作内容关注的更多是外面的世界,龙恩看起来人在大理,但似乎又和大理脱节。“我在别的城市,也不是那种特别融入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觉得我没有融入一个群体会怎么样,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常。”她说。
理想中的数字游民生活,是有稳定的稿酬,并和当地人建立更多的线下连接。龙恩参加过白族的火把节,去村民家里做客吃席,然后没有再联系过。她说自己和大理没有蜜月期。自然的风景很治愈,但是深层的精神连接更能留住她,归属感仍要落地于人和人的关系。数字游民的状态似乎决定了你能拥有一段又一段短暂的关系,然后人们如同候鸟般迁徙,归巢。
在这期间,她短暂地结交过一个朋友,一个荷兰留学回来的理工科女生,两个人一起吃饭、爬鸡足山、逛公园,对话也有了真正的深度连接,但是游民的底色就是流动,这位朋友原本在大理一家洱海保护机构工作,去年12月辞职离开大理回到了重庆。
还有另一个同样租住在这里的室友,龙恩和他一起在洱海边看过日出,一起做饭,也去喜洲古镇逛过,后来渐行渐远,龙恩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更多时间宅了起来。她尝试过向外探索,但似乎是徒劳的,现在,呆在上鸡邑村,就相对自在。

2月7日,龙恩步行20分钟即可抵达洱海边。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社群集结
我不确定龙恩的数字游民经历在游民群体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否大多数人也像她一样,安静地探索,沉默地离开,或者热闹地活着。
于是我去了一家数字游民社区NCC。NCC,是Nomad Co-living Co-creating的缩写,意思是游民共居共创。这家社区位于大理古城西门葱园村,从古城西门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达,也是一栋传统的三层白族民居,中间有天井,适合做公共空间,因为地势高,背靠苍山,三楼的房间能看到洱海。
主理人大曹已经返乡了,很多入住的游民也已经回家过年,2月份一共入住了8个人。这栋三层的白族民居,也是传统的建造格局,没有经过太多改造。我见到了几个过年不回家的游民,有的在做占卜,有的在做人类学调查,主题是大理的创新教育。
大曹出生于1994年,2022年8月离开职场,她曾经当过媒体人,也在大厂工作过。本来她想gap(间隔年)一年,然后重回职场。她去了景德镇,海南万宁,想看看脱离了职场轨道的人在干什么,有人说大理更嬉皮,也有人说很多人在这里躺平摆烂,她决定来看看。
刚开始她对大理的印象不是很惊艳,商业化的古镇和好看的民宿,后来她认识了一些常年在这里驻扎的新大理人,也看到不同的人合力一起做事的纯真,她发现,这似乎是一个有结界的地方。游客看到的,隐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个大理。她把这里称为,“流动的筵席”,一拨一拨人来人往,从最早的背包客,嬉皮士,文艺青年,摆摊客,到后来更多的中产、艺术家,媒体人定居,“当下的大理也折叠着很多圈子。”
大曹本来只是路过大理,但她留了下来,创立了数字游民社区。对于大理来来往往的数字游民们,她更像一个旁观者。“如果你不是诚心地想要去探索新的事情,就很难真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数字游民。因为数字游民要求还蛮高的,要有一技之长,也要有持续的能力,包括心理状态,你是否接受这种不稳定的,或者说从积累到长期收获的过程。”
现在,NCC线上社群已经有五六千用户,但入住是有筛选机制的,有什么技能,对什么感兴趣,是远程工作,还是自由接活,除了共居共创,这里更像一个共识社区。
最开始入住的很多都是“比较闲”的人,他们大多刚刚辞职,处于人生的探索期,也许是摄影师、设计师、自媒体人、心理咨询师。慢慢稳定之后,将近一半比例的人有持续的收入,是远程工作或自由职业。房间收费集中在1000-2000元,四人间是900元一个月。
入住者粗略的人群画像是,三分之一的人研究生毕业,70%的人从一线城市而来,他们关心社会议题,而不只是想来领略大理的风花雪月,他们都想要凝聚更大的价值。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了七八对情侣,组织了200多场活动,包括白族女性力量展、AI入门课程、各类不同职业的分享等,最大的一个共创项目是国内首届数字游民大会,甚至有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项目合伙人。
最长入住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后有人回到了原来的城市,有的在大理租下房子开启新事业,有的人带着远程工作定居下来。大曹的一个朋友在大理探索了将近一年,他没有留下来,他没办法完全抛下世俗的更常规的生活轨迹,去过一种完全轨道外的生活,他回到北京上班。

位于大理古城西门葱园村的NCC社区。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人来人往
龙恩打算离开了。她想回到广东,饮食和文化氛围更贴合自己的地方。等到手头的稿子写完,拿到稿费,积攒了可以去新城市落脚的费用,她就会离开。但仍然会从事自由撰稿,如果有全职机会也会考虑。
毕业两年,换了三个城市,高频率的变动,让她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我跟所在的城市,保持着快餐般的关系。不远不近,随时准备抽离。”
这十个月的经历,不尽如人意,但她仍然在失落中获得了一些积极认知。无论是轻体力的兼职见闻,还是线下的文艺活动,龙恩有过焦虑,也进行了有限的探索,接触到更多主流生活以外的人,“看到别人是这样生活的,就会更加确定自己所选择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
虽然撰稿机会不太稳定,但她仍然觉得视野被打开,打破了之前的惯性思维,现在她觉得主流的评价体系没那么重要。“只要可以养活自己,其实就做什么尝试都是可以的。”家里人不知道她旅居在大理,也不知道她已经过了将近一年自由职业的生活。对她的家庭来说,这是“离经叛道”的。
龙恩和大曹都觉得,数字游民不被社会时钟所束缚,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不确定,还有职业上的不确定,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探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身份。“当你向别人介绍,你不会说我是一个数字游民,你会说我是一个设计师。”大曹说。
“你离开了固定的赛道之后,没有职场的庇护,没有五险一金,其实反而很多人是很迷茫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打开你的人生,脱离这个轨道外面全是你的赛道,那你怎么去制定你的游戏规则,怎么把你的人生过得精彩,其实是一个更考验人的命题。”大曹说。
在十个月之前,龙恩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自由撰稿,租住在西南边陲一个白族村落里。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她慢慢去理解并接受这个选择,也发现或许自由撰稿就是更适合她的一个方式。如果职场氛围压抑,难以产出高质量的文章,写作能力下滑,沦为打一份工,“我需要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足够的空间,然后我才可以写出比较好的稿子。”
在2023年的年终告别里,她把自己定义为“漂浮的码字女工”,她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个人纵身一跃,跃向的不一定是确定的幸福,而是不确定但充分自主的人生”,她愿意尝试一种需要更多想象力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