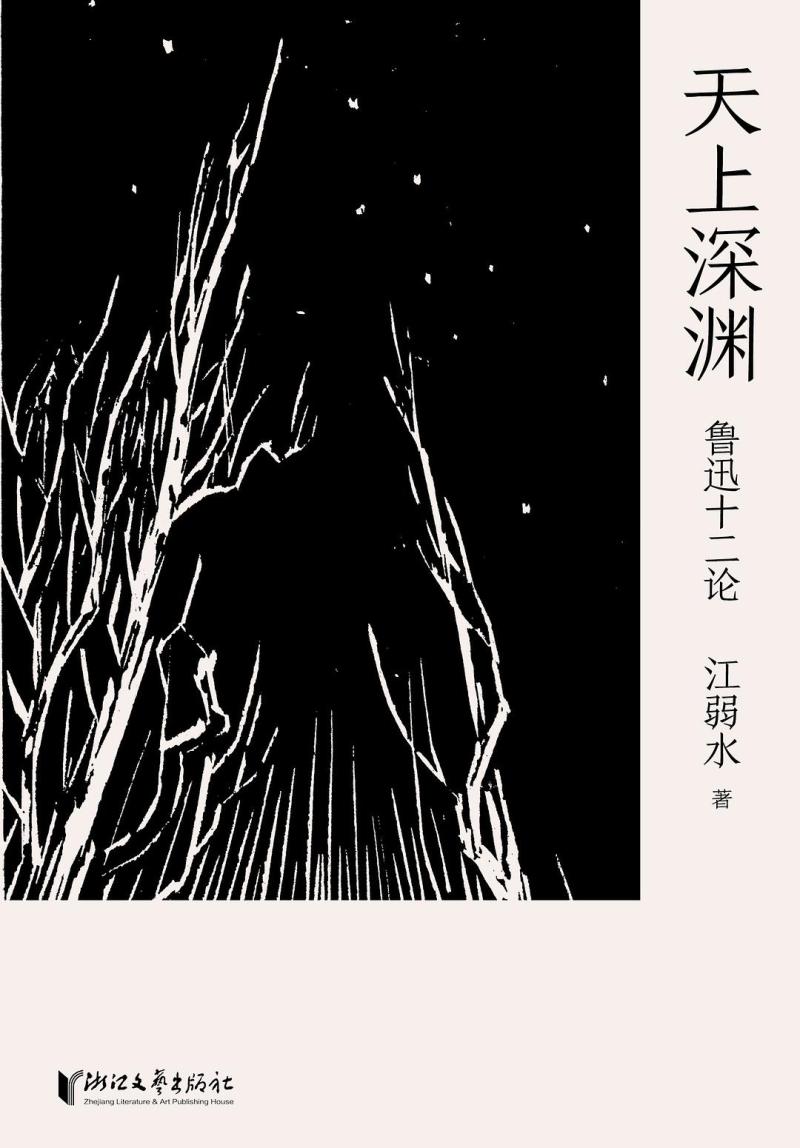
《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作者:江弱水,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鲁迅对《列子·说符》中的一个故事一定感受强烈,他两次引用了其中的谚语,“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似乎在这句话中窥知了自己的命运:
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郄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
鲁迅是一个煞风景的人。面对新生儿,他不是恭喜升官发财,而是说将来是要死的。他老是看穿假面下的真实,甚至“于天上看见深渊”。他一辈子都是一个睁了眼看的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什么幸福?因为他看见了真相。为什么哀痛?因为他看见了真相。
他也知道自己这毛病不好:“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两地书》1925年3月31日)“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两地书》1925年4月8日)“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马上支日记》)
这就是“察见渊鱼”“智料隐匿”。鲁迅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去看人生,看社会,看历史,看神圣的观念,看一切的一切,一切背后的一切。在《淡淡的血痕中》,他连用了“洞见”“正视”“看透”,这些都是“察”,一系列“看”的同义词。鲁迅的目光如此具有穿透力,他看穿了世人种种“揩油”“吃教”的行径;他戳破了中国人的才子佳人的大团圆想象和十全大补的幻觉自欺;他洞悉“凶兽和羊”两种人之外,还有一种卑怯的国民,“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他清楚那些“无特操”的“做戏的虚无党”;他预见“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叛徒给处死;他察觉“革命文学”的本质是“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他认定所谓“太平世界”事实上是晒滤掉“记忆”的、对苦难视而不见的悲惨世界。总之,他“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但是,“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所以鲁迅很苦。《淡淡的血痕中》的五百字里,重复了七个“苦”字:造物主“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而真的猛士要“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这不是陶渊明说的“人生实难”,而是他《希望》感叹的“可惨的人生”。
结果便是“不祥”和“有殃”。在“自啮其身”的一生了结之后:“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死后》里的这番话,看上去是调侃,其实惊心动魄。这就叫“不得其死”呀!“不得其死”并非横死,而是生无立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才会死在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不知什么地方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无地之地”。
我们要注意鲁迅最奇特的否定性表达。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他把意义相悖的词放在一起,在相互否定中表达出了单个的词所难以表达出的意思。“无地之地”,这是既非黑暗也非光明而且也不是两者的调和物的两间之所在。在鲁迅,这样的思维已经形成了定势,在悖论的旋涡里相互否定,相互缠绕,彼此撕裂,永无宁日。
因此,彻底理解鲁迅是不可能的,你会掉进一个悖论的旋涡,这是读者的大不幸。没有语言来做成他存在的家,鲁迅时时流露出某种无根的漂泊之感。《祝福》中的“我”说:“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鲁迅是被“剩”在“无地之地”的人,没有了家,只能不断地走,短暂的落脚点并不是永久的故乡,也不是心灵的故乡了。
回得去的故乡不是故乡。在鲁迅那里,形成不了真正的陈述,因为所有的陈述相互否定,对立的共存中充满紧张。他无法给自己的活法一个说法,怎么说都是矛盾、悖论和冲突。陈述本身成了“我在陈述”的意义,走本身成了“我在走”的意义。《野草》中,充满了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追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而鲁迅的“不祥”在于,他对于这一切,全然没有答案:“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从那里来的呢?”“到那里去么?”“我不知道。”(《过客》)“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死后》)鲁迅于是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不上,不下,不明,不暗,不走,不留:“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死后》)“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影的告别》)“携带你去”,“那么,我将烧完!”“将你留下”,“那么,我将冻灭了!”(《死火》)
于是鲁迅“有殃”。人虽生而自由,却又时时在逃避自由。人生就是在寻找依托也就是锁链的过程当中,希望获得一种观念,一种身份,一种关于自我的叙述,好在其中安心且立命。但是鲁迅并不寻求在任何名词观念上给自己安生,他因为揭破了一切虚妄的迷雾,拆解了每一个可能的遮蔽之物,抽空了一切常人赖以栖息的观念之支撑,结果,他抽空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他的宿命:“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陨颠。”(《墓碣文》)顾随说得好:“如《在酒楼上》,真是砍头扛枷,死不饶人,一凉到底。……不但无温情,而且是冷酷。”而鲁迅就是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不给自己找遁词,不为自己留退路。
中国文人的思维定势,总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总是把自己从他所指控的罪恶中摘出。鲁迅不然,他在四千年吃人的筵席上看到了自己也有一份,在其中混了多少年,不知不觉中也可能吃下了亲人的肉。“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就是鲁迅为中国人找到的“原罪”:吃人的历史我们人人有份。
那么,孩子总是无辜的吧?鲁迅也说要“救救孩子”,这说明还有“希望”。可是他后来发现,连孩子也是不可信的,不可救的,人类遗传的力量是可怕的:“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颓败线的颤动》)“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孤独者》)
未来是不可预期,不能指望的。鲁迅很早就把中国人的历史归结为两个时代,乱世固然“想做奴隶而不得”,治世也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灯下漫笔》)。魔鬼战胜天神,人类战胜魔鬼,“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失掉的好地狱》)。总之,休想指望未来的“黄金世界”。
那么回去吧。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童年,一切失去了的美好都在那。但鲁迅说,过去是会欺骗你的,回忆是靠不住的。记忆中故乡的美味,罗汉豆啊,茭白啊,这些会哄骗一生的思乡的蛊惑,待到回去的时候却全都变了味道。“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故乡》)
最后,连同情也是“放鬼债的资本”(《铸剑》)。最后的最后,连爱也是不必感激、不可回报,甚至可以诅咒的:“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我的失恋》)“况且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过客》)
总之,无法寄希望于未来、回忆、同情,或者爱。鲁迅把自己倒逼到一个“无地之地”,找不到任何可以躲避自我追杀的地方。这个对中国人失掉了希望、对中国的历史黑暗面看得太多的人,虽然在死后获得了圣人般的盛名,但活着的时候却比谁都糟糕。亲爱的母亲赠给他不要的礼物,而婚姻的不幸,又加上兄弟的反目。内心的创伤不断,身体的病痛也一直伴随着他。他不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上天也给不了他大团圆。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一生。只能一直走,走向绝望,而绝望和希望一样虚妄。
鲁迅留给自己的,最后只有死亡的快意了。所以他会说:“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他是把死亡视为对生命的复仇,对苦痛和无聊的复仇。与其偷生在一个不明不暗的暗夜里,徘徊在野花与荒坟之间,还不如奋力一搏,“奋然向西”:“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希望》)“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过客》)
“夜色”显然是死亡的阴影,“向西”的路是朝向死亡的路,而死亡是接近巅峰时刻的生命。在《复仇》中,人们用充满活力与情欲之温热的身体,互相蛊惑,煽动,牵引,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但死亡使人呼吸冰冷,嘴唇淡白,却更能“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这两种大欢喜,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与死亡给予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一个下沉,一个上扬,其间差异就像《雪》中“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处子的皮肤,以及后文的冬花,采花的蜜蜂,都有性的暗示,是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的写照。“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这是决[疒丸]溃痈的一刻,是大痛楚与大欢喜结合的痛快淋漓。“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然后是痉挛的死亡,“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复仇》其二)
生为痛苦,死为痛快。这样一个精进于地上的生命的人,曾自拟为“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濡沫于可怜的人间世,也有庄子之龟曳尾涂中的影子。但鲁迅与庄子的“养生”和列子的“贵生”格格不入,因为他俩对生命都看得太重。鲁迅到底还是认同佛家的生死观,而在佛家看来,身体的形质不过是粗糙的存在。1934年,鲁迅应日僧眉山之请写字,就写了《金刚经》中的一句:“如露复如电”。两年后鲁迅去世,死时体重只有七十六斤。没有人死得比他更少。
撰文/江弱水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