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成人类,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从纯粹的素食者变成大量摄入肉类的杂食者。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改变了人类祖先的体型与大脑结构,也改变了人类祖先的生存模式——狩猎对团队协作的要求远高于采集,狩猎与创造工具、学会用火等划时代进步的关系也更密切。可以说,如果人类的祖先没有选择吃肉,便不会进化出高度社会化的人类族群,也不会有部落与国家。然而,当部落与国家出现后,肉食者与素食者竟变得泾渭分明起来。不独晋献公用吃素者来指代被统治者,《战国策》里也说“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明言普通人难见荤腥只能吃素。甚至于统治者内部也有吃肉吃素的歧视链。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与晋国举行黄池会盟时,便遭到晋人的讽刺。晋人说,“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分明显示吴国的国力不行——墨,即脸色衰败之意。晋国是老牌中原霸主,在晋国君臣眼里,真正高贵的统治者天天吃肉必定油光满面,而吴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吴王即便同样天天吃肉也只配拥有素食者那般衰败的脸色。
面有菜色
若是能够多吃肉,百姓们自不会乐意常年吃素。故此,人类的吃素史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总体而言仍以无可奈何只能吃素的历史为主。这也是先秦思想家普遍关注吃肉问题的主要原因。孟子对梁惠王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普通百姓不受饥寒之苦,到了七十岁还可以吃肉穿帛,就说明执政者做得很好,就说明那是个很好的时代。反之,如果国君的厨房里有肥肉,牲口棚里有肥马,百姓却面有饥色乃至饿死在野外,那就是“率兽食人”的暴政。《礼记》里也有一段关于什么是好政治、好时代的表述:国库里存着超过九年的粮食,遇到旱灾水灾百姓脸上不会有“菜色”——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专食菜故肌肤青黄为菜色也”——天子才有资格在吃饭时以歌舞助兴。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时代从未降临在现实世界,先秦思想家们只能拿传说来批评现实,如《荀子》盛赞“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夏禹、商汤时代缺乏史料记载,方便了思想家们牵强附会。实则按常理推测,夏禹、商汤时代的百姓大概率也只能吃素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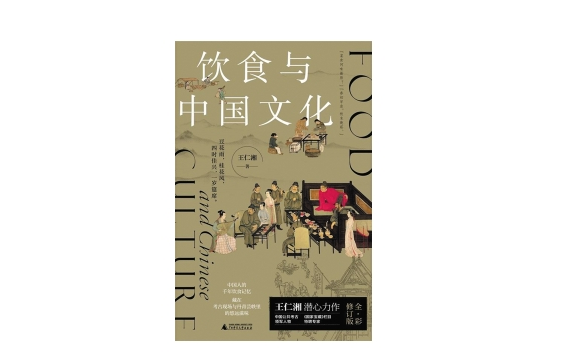
《饮食与中国文化》,作者:王仁湘,版本:新民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汉承秦制,百姓们同样很难吃上肉,仍以素食为主。儒生翼奉上书汉元帝建议迁都洛阳,理由正是关东地区因饥荒与疫病已是“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可见当时百姓的境况远不止是被迫吃素,而是连正常的粮食也没得吃,要吃野菜树皮乃至吃人了。因推崇儒学,汉代的政治场域中还新增了许多肉食者主动吃素的戏码。原本肉食者主动吃素仅限于丧葬祭祀(后来又增加了宗教因素),如霍光废黜昌邑王的理由之一正是“居道上不素食”,前任皇帝丧事期间不肯吃素而继续大鱼大肉,可见实在不配做皇帝。讲究以民为本的儒学盛行起来后,官员们便也纷纷主动营造吃素的人设,以彰显其与民共苦。如王莽贵为辅政大臣也是“每有水旱,辄素食”,非得太后派了使者来求他“爱身为国”才肯开戒吃肉。杨震官至太尉,也是“子孙常蔬食步行”,实则若非自己刻意宣传,太尉府里是吃素吃肉,外人既不感兴趣也很难知晓。
恶衣蔬食
肉食者们愿意表演吃素,是因为大多数普通百姓只能吃素。毕竟与民同乐时百姓未必真乐,与民共苦时百姓却是真苦。据《后汉书·和帝纪》,汉和帝曾下诏命令郡县“劝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又允许地方郡国的流民去官府控制下的陂池采集“以助蔬食”,可见当时普通百姓不但没肉吃,连五谷杂粮也不够,官府只好号召大家搞瓜菜代。三国时代是肉食者表演吃素的一个高峰期,如董和担任成都令“恶衣蔬食”,国渊“居列卿位,布衣蔬食”……这自然也意味着普通百姓的饮食状况变得更差了。吴国使者薛珝前往蜀国求马,对蜀国政治的印象是“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后来司马昭派军队灭蜀,任命王濬为巴郡太守,王濬到任后发现巴郡百姓“生男多不养”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可见蜀国百姓不但被迫普遍吃素,而且根本吃不饱,以至于连孩子都不愿意养了。吴国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孙皓当政期间,中书令贺邵上书批评政治黑暗,提及“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而吴国百姓却是“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这直白严厉的批评没有引起孙皓的反思,而是给贺邵带来了杀身之祸。
民有菜色的悲剧在帝制时代从未间断,肉食者与民共苦的戏码自然也不断重演。剧情相似不必赘述,惟有两事颇值得一记。一是神鬼也不肯过吃素的生活。事见《朱子语类》。据朱熹说,四川灌口二郎庙原是祭祀修筑都江堰的李冰,后改祭李冰次子李二郎。这李二郎本受封为王,后因宋徽宗推崇道教,遂将之改封为真君。张浚统军抗金时,曾前往二郎庙祈祷,随后夜间梦到二郎神来传话:“我向来封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号为真君,虽尊,凡祭我以素食,无血食之养,故无威福之灵。今须复我封为王,当有威灵。”由此可见,在宋人的认知里,连神鬼也要吃肉才有神通。这也正是南宋的灌口二郎庙常年杀羊祭祀、庙前羊骨堆积如山的缘故。需要注意的是,今人常以《东京梦华录》为依据来佐述宋代繁华,殊不知《东京梦华录》的作者是个官二代,肉食者的繁华不等于普通人的生活。另一件事发生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以盗取军粮十万石的罪名冤杀了户部尚书滕德懋,还派人将滕的妻子王氏逮捕并亲自审讯:“你的丈夫贪污军粮十万石,按律当死,你有什么想说的?”王氏答道:“我丈夫确实该死。盗取那么多粮食,居然不拿一升半斗回来养妻儿子女!”朱元璋追问“那你吃的是什么?”王氏回答“藜藿耳”,意思是天天吃素。朱元璋大怒,命人诛杀王氏并将其剖腹,结果王氏腹中真的只有“粝食菜茹”。可见洪武时代号称治世,却是个连肉食者也不一定吃得上肉的时代。
告别吃素
世界其他地区也都经历过漫长的素食时代。比如英国,一般认为要到16世纪才开始渐渐自素食时代转至肉食时代。16世纪中叶的英国士兵与水手每天可以获得1.2至2磅盐牛肉。穷人也可以吃到牛肉、羊肉和培根,但吃得更多的是牛奶、黄油和奶酪等奶制品。因为当时的英国上层社会追求鲜肉,认为奶制品是乡下人和仆人才会食用的廉价物。这场饮食结构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新航路开辟给英国带来了贸易繁荣,整个国家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可惜的是,中国与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也错失了工业革命的红利。故而素食时代的延续格外漫长。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年间来华时,已注意到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仅为勉强糊口,因肉食奇缺故而“即使是腐烂了的(肉)也不放过”。晚清民国政局动荡战乱频繁,民生状况变得更糟,所以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仍是素食者。民国著名的主动吃素者丰子恺先生曾哀叹“世间自动的素食者少,被动的素食者多”,因被动吃素往往意味着穷困潦倒。据他所见,民国是个全民被迫吃素的时代,“现今乡村间这种人很多,出市,用三个铜板买一块红腐乳带回去,算是为全家办盛馔了。但他们何尝不想吃鱼肉?是穷困强迫他们的素食的。”他还说,现今“城乡各处盛行素食,‘吾道不孤’,然而这不是我所盼望的!”

调查资料也颇能佐证丰子恺的观感。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调查了重庆240户工人家庭。结果显示这些家庭以大米和红薯为主食,蔬菜消费以白菜与萝卜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此外还会吃一些魔芋、莴苣、青菜、南瓜、榨菜等。肉类消费则极少,平均每户(户均3.6口人)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牛肉鱼肉等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张闻天1942年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发现当地的中农家庭只在每年的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还有二十三日,有机会吃到“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他时间都是吃素:“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后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来时,还吃些山芋。秋收后,又只吃二顿,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1944年的驻滇远征军号称中国饮食标准最好的部队,也仍是以素食为主,仅“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同年,美国卫生专家在滇缅战区随机抽取了1200名中国抗日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这种营养不良,其实就是古籍所载的“面有菜色”。
中国人告别素食时代是近几十年间的事情。1980年,中国的人均年肉食消费量是12.79公斤,1990年是20.1公斤,2000年提升至城镇年人均消费量27.4公斤,农村17.44公斤。这场饮食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与改革开放完全同调。
撰文/刘三解
编辑/李阳 宫子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