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倦怠社会:韩炳哲在首尔和柏林》(2015)画面。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无疑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学者。过去五年间,他的18部作品被先后译介到中文世界,其中对当今社会的病理式剖析引发广泛讨论。与此同时,韩炳哲本人却极少在公众前露面。2015年,他以自述的形式出现在一部纪录片《倦怠社会》中,片中呈现了他在家乡韩国首尔和德国柏林的漫步旅程。这也是对韩炳哲思想世界的一次电影化展演。
在“韩炳哲热”的今天,或许是时候反思,这种介入现实式的写作为何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以及时至今日,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韩炳哲对这一代人的剖析论断?这部纪录片提供了另一种补充性的视角。
近日,中信出版集团与北京大学会议中心合作,在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了由伊莎贝拉·格雷泽拍摄的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传记型纪录片《倦怠社会》。放映结束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戴锦华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就纪录片与韩炳哲已经出版的中文作品展开了对谈。这场对谈由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黄竞欧主持。以下为本次对谈的节选内容整理。
1.韩炳哲比战后法国理论家走得更远
黄竞欧:就我阅读韩炳哲的体验而言,虽然他是德国的学术背景,但是他好像更接近于一种法式的写作。李洋老师是否认同我的判断?您觉得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的求学或者生存的境遇对学术气质的养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洋:我不知道说“法式”是否合适,现在好像大家要说话要谨慎一点。萨特是现象学的传统代表人物,他去德国听了现象学的课,回法国后就写了存在主义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他认为我们不要做大学里、金字塔里形而上学的哲学,要跟今天的人的生活有关系。“哲学应该在大街上”,这是《存在与虚无》导言中的话,如果说这是法国哲学的特点,韩炳哲是符合的。
二战后的法国哲学家都积极介入到社会生活,如果哲学还是经验的、学院的,它的生机就会萎缩,只有它跟人、跟生活、跟年轻人的困惑发生关系时,才能焕发能量。所以二战后的很多哲学家关心现实,他们的哲学思考、训练与他关注的现实总是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决定了他们讨论什么问题,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韩炳哲经常引用德国的哲学经典,比如黑格尔、康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但他也经常会讨论福柯等法国哲学家,讨论当代问题,他的写作方式和面对大众的态度很像法国思想家,具有法国哲学的特点。我的留学生活好像没有对我学术气质的养成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我是觉得韩炳哲可以悠闲地在德国、韩国,很闲适、没有压力地思考和写作的状态非常令我羡慕。在法国有人会在咖啡馆里闲坐一下午,尽管我在法国留学了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像他一样享受过咖啡馆这种空间的感觉,或者社会给他提供的那种状态。

纪录片《倦怠社会:韩炳哲在首尔和柏林》(2015)画面。
黄竞欧:戴老师如何评价他这样一种写作的方式?
戴锦华:我们总会一言以蔽之说“欧洲思想”或者“欧洲哲学”或者“西方哲学”,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具有差异性的内部的相互对话。至少19、20世纪,尤其20世纪的欧洲思想的发展都主要发生在法德对话之间,有时英国会有一点份额。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在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人的著作中看到某种法国的印痕,或者在法国的学者身上看到德国思想家的痕迹,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但总的说来,我并不觉得韩炳哲是法式的写作,之所以我们会产生法式的这种印象或者感觉,其实就是刚才李洋老师说的,是韩炳哲对现实的敏感,对现实、当下的关注,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这样一种介入。就像纪录片当中,他漫步在墓园,漫步在废墟,其实是在都市和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被焦虑和忧郁症的浪潮所淹没的社会之外或旁边。他这样的位置和写作本身,正好会更清晰地表现出置身在某一种距离之外,但是保持很强的关注度。可能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会觉得他有某种法国理论的意味。
其实法国理论就是指战后这种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介入性的动能,但不同的是,战后的法国理论家把所有的现实都隐藏在他们的高度哲学的、强烈的对话,和以黑格尔、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传统的学院的、规范的话语逻辑中,只是经由法语变得更缠绕和繁复,现实并不直接在文字的表层上登场。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于那一代法国理论家的影响是极端深刻和内在的,但是他们很少付诸在行文中。
在这个意义上说,韩炳哲比所谓战后的法国理论家走得更远,因为他直接在讨论当下,直接在讨论新技术革命冲击之下的全球化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现实,在改变着所有的个体的生活情况,他直接在讨论这些议题。他在讨论“点赞”,他在讨论“内卷”,他在讨论“信息疲劳综合征”,所以他并非法德任何一种所谓哲学传统的逻辑延伸,这使他很独特,这也使他不能得到如哲学圈,或学院主流的认可。
我读韩炳哲时有一个小的系谱,先是鲍德里亚,他是以学术性的写作为生、而在学院体制内没有占到重要的位置的一位法国学者。另外一位是近年来在东亚,甚至在世界上都非常火爆的东浩纪,他有自己的文化公司,逐年在进行新书的写作和出版,接下来就是韩炳哲。三个人非常像,他们的写作量非常大,他们对现实的指认、介入、分辨、勾勒、命名非常直接,但是他们并不在学院体制内部。如果我们写一本当代文化史,这些人都不能缺席,但如果写一本当代哲学史,他们未必能有位置,你是哲学背景,你最有发言权。
2.酒吧、节日与二手商店:韩炳哲笔下的堡垒意象
黄竞欧:韩炳哲在电影里面说他经常去《柏林苍穹下》中拍到的二手商店和酒吧。我想先问问戴老师,您生活在北京的时候,您有没有类似的书店、公园这样的空间,进行像韩炳哲一样的独处?
戴锦华:我太老了,我会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去咖啡馆,会和他们在那约会,但是我从来不是一个会在咖啡馆写作的人。
我不会在这种空间独处,但是我会在比如说北大校园,或者某一些不是公园的绿地的空间,我会在那里长时间地走路、拍照,那种是会让我感觉到独处和沉思的时刻。
黄竞欧:接着这个问题还想问一下李洋老师,因为韩炳哲有一个判定,他觉得二手商店是一个对抗消费主义的堡垒,可能相对于同质化的、满街都是便利店的情况来讲,在那里主体才会更加的活跃。您这么看他对于消费主义的判定,或者二手商店会起到一个对抗堡垒的作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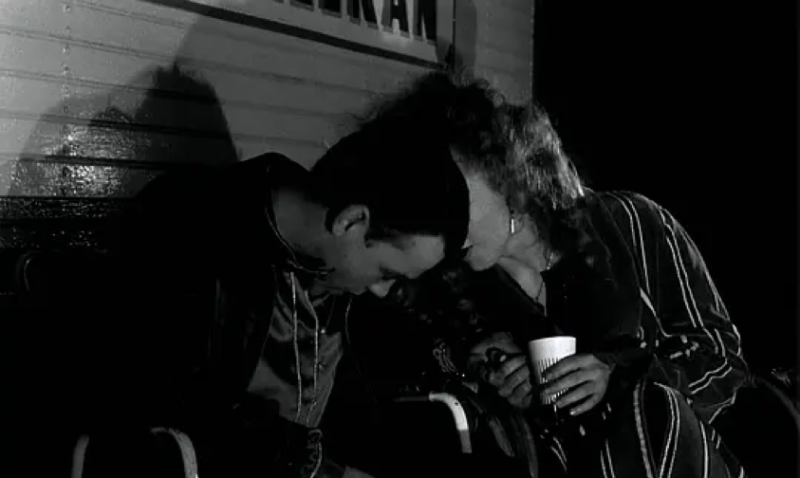
电影《柏林苍穹下》(1987)剧照。
李洋:我的经验里有两种二手商店。
一种二手商店,它的目标的消费者不是我,是那种特别有钱的,我在法国曾经进入过那种二手店,我想淘点便宜货,进去之后发现走错了地方,那些东西是二手的,但我还是买不起。这种可能加剧了消费社会,旧的东西比新的还贵。
还有一种就是我常去的二手书店。欧洲的二手书店里一本书两欧元、三欧元,非常便宜,我就会经常去买两本书。
所以我倒觉得,他说二手店也许是指,有一些消费主义的物质产品被生产出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但是它的主要的目的被剥夺了之后,虽然它已经被淘汰、废弃了,但还能用,可我们不用。比如手机,旧款的手机其实还可以用,但消费社会不断让人们盲目追求新的价值,大量的物质生产品就被“淘汰”,物品就被当成废品来对待,事实上它并不是废品,这时候它恰恰焕发了非消费价值所带来的新的光辉。
比如老旧的式样,我就拿一个诺基亚,我用的不是手机,而是老旧的式样,或者再拿一个什么二手的东西,我完全不在乎它作为机器、作为商品的功能,我恰恰要看它的体验,它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强调这种所谓的被废弃之后的美感体验,或者说被高速运转的消费社会淘汰的那些东西,它依然所能够被发现的价值。如果是这个的话,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黄竞欧:也就是它们可以构成某种堡垒。
戴锦华:纪录片当中,他援引了两个作品和一位导演。他援引的作品一个是电影《柏林苍穹下》,另外一部就是我一直努力地推销、宣传的一本小书,但好像大家的回应一直都不太强烈——德国童话《毛毛》,副标题叫“时间窃贼和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是20世纪50年代写的书。
我觉得《毛毛》可以被认为是对今天这个越来越急剧加速的现代社会的智慧的预言。
一旦我们开始关注怎么样节约时间、追求效率,恰恰就证明着我们正在因此失去“时间”,我们的生命被榨干,而那个时间都存入了小说中说的时间银行,而那些时间窃贼正是以我们的时间为生,我非常喜欢这本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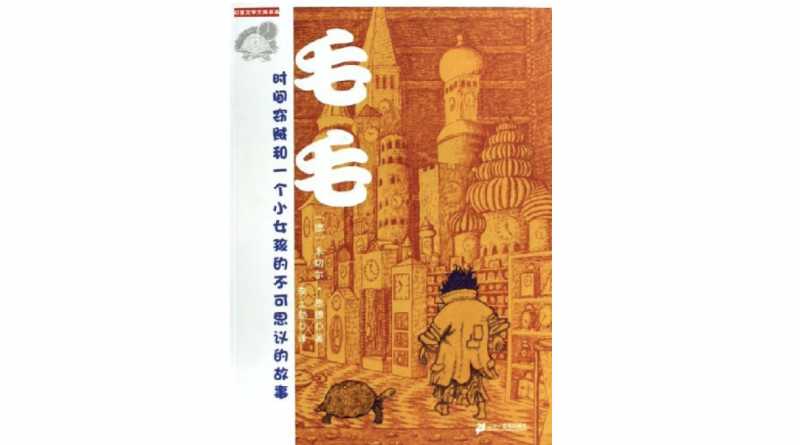
《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作者:[德]米切尔·恩德,译者:李士勋,版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
另外一个东西是二手商店,我觉得大概有三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有一些二手商店真的是济贫性质的,比如说欧美的救世军,穷人大概3到5美元可以买到一件衣服御寒,我觉得这是一种。
第二种二手商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韩炳哲体验的由来,我知道韩国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整个韩国组织起了一种二手商品流转的物流和商业中心,就是把崭新的、退流行了的衣服,或者大量的批量生产的但因为积压而变成了废品的东西集中起来,然后让低收入的家庭都能够买得起这些日常消费品。
第三种二手商店,是李老师所说的那种,叫古董店。
这个古董店就非常有趣,我感觉它们很少具有美感,但是价格极端昂贵,原因是在于欧美资产者的心理情结,他们非常怕自己表现出资产者的趣味,比如说用大量的不锈钢的、光亮的、机械感的家具,而一定要用旧的。
我最近发现,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的机关单位的档案柜突然开始变得非常流行,你会在金碧辉煌的私人住宅里面看到这些档案柜,它以旧为美,以岁月感、时间感为美,因为这样“我”就表现出和新的暴发户的、新的资产者的并不高级的审美趣味的区隔,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消费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是用一种方式来区隔出谁是更有审美趣味的消费者。
特别是如果你一进门看到满屋都是宜家会很没有面子,这说明你一定是一个刚刚就业的,刚刚涌入城市的小中产者,或者勉强悬挂在中产者的边缘上的。
如果一堂旧家具代之以各种各样的趣味的表现,那么你就把你的新钱变成了老钱(old money),好像一下就有了身份和地位,其实只是拜金主义的变形而已。
我想韩炳哲倡导的应该是前两者,应该不是后者。

电影《柏林苍穹下》(1987)剧照。
黄竞欧:很多哲学家会谈到关于节日的问题,韩炳哲在他的作品里也很喜欢提到,韩炳哲觉得节日是一种自我表达,因为节日是不追求任何目标的丰盈的生命的体现,所以我们会庆祝节日,但我们不会庆祝劳动。只不过在韩炳哲看来,现在的节日更多地变成一种大众性的活动,或者消费形式。
想请问两位老师,平时会过传统节日或各种各样的节日吗?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时间节点是您觉得需要庆祝的吗?您怎么看待某种很明确的以消费为导向的节日,比如“618”或者“520”这些所谓打着引号的“节日”?
戴锦华:过节在我的个人记忆中是一个渐次褪色的过程,可能跟年龄有关,也跟整个社会变化有关。小时候期盼节日,因为只有在中秋节才能吃到月饼和家里做的多层的、放果料的甜糖饼,会盼望除夕晚上,外婆魔术般的拿出酥鱼、各种果仁。一年中可以一直期待这个神奇的夜晚到来,可以不睡觉,到12点再下一次饺子,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一直吃东西,可以把瓜子皮、花生皮丢在地上,名曰踩碎,大家走在上面吱吱作响。太多的仪式、满足感和亲情在匮乏时代被放大了无数倍。
小时候腊八节会煮大锅的腊八粥,当时北京很冷,就会切成很多块,小孩负责每人拿一块去送给邻居,邻居家会有同样的一块还回来,最后会吃到一条街上不同人家的腊八粥,小孩们会刻薄地评价谁家放的枣太少,谁家放了很多花生和栗子。这样的经历随着长大就在逐渐淡去,从我们开始到商店里买,到现在对我来说中秋节就是一个灾难,因为无数口味的月饼同时到来,特别奇怪的馅儿,翻出花来的馅儿,或者根本就是冰激凌或者蛋糕。它原本包含的情感、仪式、记忆、节庆、亲情在淡去。
尽管如此,我觉得传统节日仍然有很多含义,比如清明节、春节的团聚,尽管红包会使一年的储蓄严重受损,但你还是乐意和亲人们至少有这一次的相聚。而像“520”这种跟节日没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些营销商品的借口或节点。但据我所知,好像每一个平台的商家都说自己因这些节日受损,所以我想知道谁获益了,可能GDP获益了。因为即使买进即刻退了货但仍然会计入到金钱流动的记录中。
3.如何看待韩炳哲对这代人的判断?
黄竞欧:韩炳哲所带给大家的某种共情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面一直针对福柯的“规训社会”,韩炳哲认为规训社会过时了。当然规训社会本来指的也是17、18世纪的状态。韩炳哲觉得在他所谓的功绩社会里,我们是自由化的,因为我们没有被规训,但这种自由并没有带给我们幸福,反而使我们越来越内卷,使我们自我剥削,变成了同样的主体。
我其实想问,比如说年轻人的这种所谓“放假羞耻”或者“无聊恐惧”,戴老师在您平时接触到的学生或者年轻人的身上,您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吗?或者您觉得韩炳哲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判定跟您是契合的吗?
戴锦华:还是再重复一遍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和我的一个基本立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有权力整体地判断一代人,因为个体差异太强烈了!我觉得韩炳哲也并没有在描写年轻一代,他在描写整个社会的状况,不仅年轻人,可能包括老人。
我是觉得规训社会的消失可以两个方面去考虑。
一个方面实际上在福柯和德勒兹共同工作的年代,他们已经预言了转变的发生,规训社会之后是监控社会,在监控社会我们更自由了,也更不自由了。自由的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在实践层面出卖自己,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劳动,包括我们的智慧,包括我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层面。而另外一个层面,自由的含义就是反抗奴役。
如果我们说自由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旗帜,它的含义是反抗奴役的话,那么在监控社会我们就更不自由了。所以在福柯的对话角度上,他所说的自由是指各种各样的自我雇佣的谎言和自我雇佣的幻觉。
而另外一种更广泛的普遍的自由实践就叫做追求财务自由。我看过一个小的材料说,在北京实现财务自由的硬指标是什么?是有房子之外还有2000万的存款。怎么能达到这种自由?我想了想就放弃了,我就说我肯定不能自由,自由离我太遥远了。
所以我觉得韩炳哲说的是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就是我们幻想自由,我们为了赢得自由而把自己套在枷锁里面,把绳子套在自己额下,去拉磨、去拖车,以为我们可以最终赢得自由,他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谈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觉得这种状况其实无关一代人或者几代人、一个地区或者整个世界的人的精神状况,而是一个结构状况。就是被新技术、数码、互联网、全球化所改变的整个世界的资本结构,所有的这些东西使我们都处在自由的、被奴役的状态之下。

纪录片《倦怠社会:韩炳哲在首尔和柏林》(2015)画面。
当然你说太阳底下没新事,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如此,但是又不这么简单。我觉得韩炳哲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确实可以用很多既有的观念和知识来解释我们的现实。但从另外一方面,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面临着现代文明前所未有的一种格局、结构、状态,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但从来没有真正把整个世界都组织在资本的生产和资本的版图之下,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经由互联网获得便利,但是同时获得了这样的隔绝。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享有很多的便利和自由,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确认的主体位置,我们甚至丧失了一种使自己成为主体的渴望。但是当你丧失了这种自我主体化的可能性的同时,这个世界没有给你提供一种可替代的、让你来安放自己的、让你能够惬意地诗意的栖居,或者是不那么诗意的,安然的、悠闲的、快乐的生活的这种可能性,这才是问题。
我觉得总体说来,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都在改善,总体说来世界上饥饿的人口在减少,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快乐,相反大家越来越不快乐了,抑郁症成了全球性的流行病。所有的这些就返回到大的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上,而不单纯是一个个体心理和个体生命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韩炳哲最强有力的地方,他在直接面对这些新的状态,而且去阐释这些新的状态。同时他的无力也就在于,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状态,试图有一个全新的阐释总是不够的,总是没有那么多的思想资源来支持和保障的。
李洋:我接着戴老师说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自由其实是一个自由的幻觉,就像你说的,其实福柯理论的模型早就在德勒兹那时候就已经被说出来了,其实不轮到韩炳哲去做这样一个判断。但问题是什么?我觉得,生命体高度的信息化之后其实就谈不上自由,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生命信息经过疫情都被信息化了,我们的行动、轨迹,包括血型,我们生命中所有能够变成信息的东西都已经进入到信息网络当中了。
因此这个时候,你作为活的生命体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网络,看上去自由,其实是一种高度的不自由。你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克制这种脆弱。
现在我跟学生接触的时候,他们都说自己是社恐(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假的),社恐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很脆弱敏感。
戴锦华:“脆皮大学生”嘛。

纪录片《倦怠社会:韩炳哲在首尔和柏林》(2015)画面。
李洋: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他一方面是自由的,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很容易被强大的机制所碾碎、所忽视、所破坏,所以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关于自由,韩炳哲只说出来了一个因素,他没有说出另外一个,就是主体性的问题。
但是戴老师,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不同的体验,就您刚才说快乐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现在的人,尤其是在这种高度消费的社会,其实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在这种机制下会痛苦,所以他尽可能宣扬一种逃避痛苦的观念,比如说健康高度至上。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掉自己的一些嗜好,对吧?比方说我们就不能饮酒,因为不利于健康。那么遇到痛苦的时候,出于健康的原则该怎么办,人就会很自然地去追求一些非常便捷的、廉价的快乐。比如短视频,我就发现它真的很容易就会让人快乐起来,你疲惫了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就会刷刷短视频,这跟人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也跟你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是觉得快乐,然后你很快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第二天可以如常参与劳动。
戴锦华:这么神奇啊,还能恢复呢。
李洋:我感觉是这样,韩炳哲有一个概念叫“平滑”,通俗点解释就是“廉价的”,随处可见的快乐输出会让实际上比较痛苦的生活看上去比较平滑,比较顺滑。当然这个快乐也许是一种短暂的安抚剂,它是布洛芬,只是退烧不能治病。至于到底该怎么治这个时代的病,他并没有提出来,也许可能是需要我们共同去思考这个时代的一些内在症结。
所以有一些人在提,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这个时代的痛苦,虽然我们都想回避,但是它唤醒我们生命的意识。
作为一个存在最不可替代的东西就是你的痛苦,因为痛苦是最真实的,会焕发你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意识,哪怕这非常渺小。所以,我们要珍惜这种平滑的快乐年代里的那些微小的痛苦,这种体验会让你唤醒你自己的生命意识。
但是,好像韩炳哲他没有说这个问题。
戴锦华:对,我觉得韩炳哲的意义就是在于,阅读韩炳哲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我特有的问题,不只有我遭遇了这些状态,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或者说对我来说阅读韩炳哲有一个收获,就是原来大家在一起痛苦啊,原来大家都挺痛苦的。
李洋:但感觉我周围的人都并不倦怠,他们都卷得充满了激情,像打满了鸡血一样。我也自己不敢倦怠,刚才那个关于过节的问题我都不敢回答,因为我过节那天晚上还在看书写东西,我过节都有负罪感,我觉得他们在让我消费一个虚假的节日,我就不接受你的节日,我就要干点正经事,就是看书写作,但事实上又陷入到工作的陷阱当中。
戴锦华:难怪李洋老师的成就比我高这么多,我即使不过节都经常让自己过节。
李洋:很遗憾这么努力,成就还这么低。
对谈嘉宾/戴锦华、李洋、黄竞欧
整理/申璐
编辑/罗东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