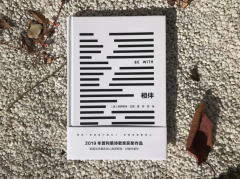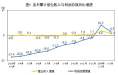撰文丨聂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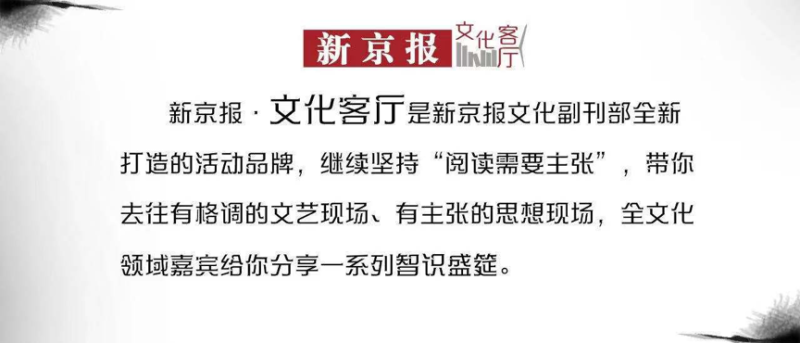
骆一禾、海子、西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并称北大诗人“三剑客”,其中,骆一禾不仅是杰出的诗人,也是最优秀的诗歌编辑与诗歌批评家之一,但相对被无限神话的海子,对骆一禾其人及其诗歌价值的发掘还比较少。近日,骆一禾生前写给妻子张玞的私人书信集整理出版成书《骆一禾情书》,从这部书信集里不仅可以看到骆一禾与妻子的爱情故事,也能看到骆一禾对诸多文人、文事的评论,从中可以一窥诗人的文思与精神世界。
我们如何理解骆一禾的诗歌价值,我们如何看待海子和骆一禾在读者接受上的不同?我们如何看待诗人之死?近日,新京报·文化客厅第二十四场联合东方出版中心、码字人书店,邀请到骆一禾的妻子张玞,以及其挚友、著名诗人西川,一起对谈情书背后的故事与“三剑客”的诗歌岁月。
如果不熟读骆一禾,对海子的某些结论是存疑的
西川谈到,《骆一禾情书》展现了骆一禾的丰富性,让他脑海中重新浮现出一幅清晰的骆一禾肖像:在北大校园里,骆一禾穿着褪色的中山装,一双白球鞋,兜里揣着自己和别人的稿子,四处和人谈论思想,在圆明园里办活动。
在骆一禾身上,西川感受到青春的力量与思想的力量是并存的。而当我们讨论文学和艺术,更多关注于恶的丰富性,一般来说,思想是与恶走在一起的,恶有各种形式,花样翻新,而善是趋向于平庸的,但骆一禾身上有一种善的丰富性,为我们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让我们看到思想的复杂性是可以和善走在一起的。
此外,当我们讨论骆一禾,我们总是会谈到海子。西川认为,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读者群,海子拥有广阔的读者群,但他的读者群并不一定就是骆一禾的读者群,两人的读者群只是部分重叠的。相对而言,海子的相关研究、传记迭出,但这些研究者或许熟读海子,却不一定熟读骆一禾,因此,这些研究或许是存在缺陷的,对海子的某些论断与结论或许是存疑的。因为在写海子的传记时不仅要把握大的时代环境,也必须把握海子生存的小环境场,而不了解骆一禾,难以说对小环境场有全面的把握。
骆一禾的相关研究目前还较少,西川认为他的诗歌价值还有待挖掘。现有的很多研究虽然将自己装扮成理论,但更多还停留在抒情性的层面,很多理论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抒情。此外,骆一禾在后期写了很多长诗,这些长诗具有前瞻性,但在读者的接受上有难度,很多读者实际上“有点接不住”骆一禾的这些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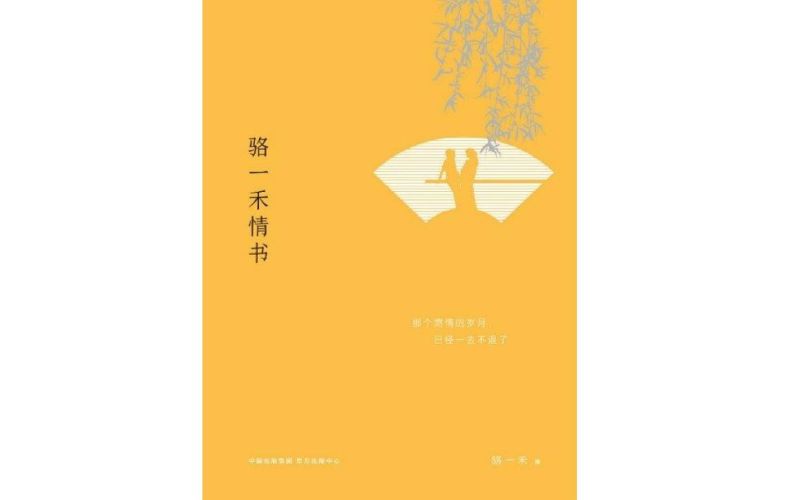 《骆一禾情书》,骆一禾著,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10月版
《骆一禾情书》,骆一禾著,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10月版
张玞也认为,海子和骆一禾晚期的长诗都存在读者接受上的问题,而她的一位诗人朋友曾经对她说,骆一禾的诗很难模仿,但海子的诗恐怕是可以模仿的。《骆一禾情书》是很容易理解的作品,如果读者透过这本书先了解骆一禾,或许也能更好地理解骆一禾的诗。
诗人的自杀不是一种谈资
西川谈到,在年轻诗人的写作里,“我”常常是非常强烈的,而骆一禾曾说过“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他的“我”是非常大的。
张玞也认为骆一禾的这种生命哲学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和对诗歌的态度。此外,骆一禾怀有对诗歌的远景想象,他后期全身心投入于长诗的创作中,是在世界诗歌谱系与史诗系统里来创作的。中国的古诗没有世界诗歌的背景,而骆一禾希望将诗歌放置于世界体系中,将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结合。
西川谈到,现在写长诗的诗人很少,很多写长诗的人认为他的诗写了上下五千年就是长诗,但那并不是长诗,只是一堆材料,而写作者用诗歌甚至称不上诗的形式将这堆材料整理了一遍。
骆一禾、海子和西川曾经谈论过长诗和组诗的区别,他们认为组诗没有长诗的结构。海子曾说,组诗是一种层岩结构,就像岩石一层一层,这种结构和长诗的结构是有区别的。
西川坦言,虽然和骆一禾、海子交往很密,但他和海子、骆一禾的文学想象和创作方向很不一样,他也并不认为两人某些时候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比如海子的直觉很好,他的文学判断从某种“已经开始有点发霉的”文学序列中“一下子蹦出来”,但是他的判断没有推理,有些判断“我是不会往心里去的”。譬如海子不喜欢庞德,认为他鸡零狗碎,但西川非常热爱庞德,他认为海子热爱的东西不够有当代性。

活动现场
现场有读者问到,海子和骆一禾相继去世,西川是否也曾想过自杀,是否曾抱有羞愧感。对此,西川回答,凡是没有自杀的人实际上都无法谈论自杀这件事,自杀并非一种谈资。海子的自杀早有端倪,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似乎有一种自杀情结。骆一禾并非自杀,但两人的死亡对西川的影响很大。
在整理海子遗稿时,他诗歌中的尸体、头盖骨等意象常常让西川倍感折磨,他常常不得不停下来。人的求生本能让他选择了一条与海子不同的路,“我绝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话,眼看着也是这么一条道。”他们的死亡加大了西川与他们的不同,在此之后,他对世界和文学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张玞则表示她对谈到活下去的人是否带着羞耻感感到不解,因为活下去是一件需要非常勇敢的事情。
中国的文学教育:缺乏对世界文学现状的认知
西川还谈到,很多读者对于诗歌的想象还停留在上世纪乃至唐诗宋词,很多人以为自己读了唐诗宋词,或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比如雪莱、拜伦、普希金或是冰心,就可以讨论当代诗,但他们的审美趣味还停留在上世纪30年代的徐志摩、林徽因,停留在“你是人间四月天”。西川说,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引用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来回复这样的读者。
西川指出,很多“大师”翻译中国古诗备受吹捧,但他们在西方根本没有读者,因为他们使用的是19世纪的语言。

骆一禾与妻子张玞合影
此外,左翼文学也影响了读者对诗歌的认知。中国现代或者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左翼文学的文学史,虽然其中不乏鲁迅等伟大的作家,但很多左翼“文艺青年”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西川曾在纽约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下课后,曾有学生问他,中国的某位作家为什么会写出这么蠢的诗。
西川直言,中国的文学教育存在问题,我们对于文学的阅读完全没有现场感,缺乏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学现状的认知。我们如何进入现代诗,如何理解现代诗?第一点就是将自己变成一个现代人,然后再将自己变成一个当代人。至于具体的建议,他认为不妨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开始阅读。
作者 | 聂丽平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薛京宁
录音整理 | 郑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