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重木
4月12日,财新网刊发报道《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疑云》,报道从性侵嫌疑人鲍毓明角度讲述这一事件。其中潜藏的一个观点便是,指出李星星并非如此前报道中所谓的那般“无辜”或毫无自我意识。《财新》记者还根据鲍毓明所提供的李星星发给他的信息,指出后者对鲍也存在爱恋,因此也就佐证了鲍毓明自始至终所强调的、他与李星星之间是“恋爱关系”,故不存在性侵一说。
报道刊发后,引发极大争议。4月13日晚间,财新网发布官方声明,称报道确有采访不够充分、行文存在偏颇之处,已在当日撤回报道。
近几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涉及性骚扰、性侵和强奸等社会事件频发,使这一始终存在又总隐在阴影中的行为,一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与其说鲍毓明事件是特例,不如说它其实只是这一系列层出不穷事件中又一个令人悚然的典型。而围绕着此次事件所产生的无论是关于鲍毓明,还是遭到性侵的女孩的言论、行为和形象的言论之中,也再次呈现出某种我们之前反复见到的摩擦、分歧和暧昧。
对受害女孩李星星的关注,除了哀其不幸之外,围绕着她的遭遇也出现了诸多质疑。尤其是对某种“完美受害者”的想象,将她推到舆论中心,遭受着检验,也遭受着二次伤害。这悄无声息地转移着涉事者鲍毓明的责任,也映射着潜藏在性骚扰、性侵和强奸之后的性/别文化、制度以及其意识形态内的种种问题。
1
看似私人的“性”:
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财新》报道所引起的质疑和批评,最终以其发布道歉且撤稿声明完结。但也以《财新》这篇报道为典型,我们在网络以及社会场域的讨论中发现,这样质疑受害者的观点和声音层出不穷。尤其在这样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中,许多人更是拿起放大镜来检验受害者的一言一行,而只要发现有任何的前后矛盾、局限或是与事实有出入,便怀疑和指责受害者可能存在“仙人跳”或是为了诸如金钱、利益等目的而设计陷害了(男性)犯罪嫌疑人。
这些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背后所潜藏着的正是我们生活其中,但又常因其无声无息而难以察觉的性/别制度与意识形态中的种种机制和问题。在诸如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看来,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性别制度本身是一套用来塑造男女两性、性别气质以及其性别(gender)的脚本,其中充满了各种禁忌与区隔、等级之分和道德预判。因此便出现了所谓“真正的男人/女人”这样的观念,以及“何谓纯洁的性?何谓肮脏、需要被排斥的性?”这一划分。鲁宾指出,在这一性别制度中,作为建立在性别二元本质基础上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有别且低于男性的存在,因此对其的约束和规训也往往远严苛于对男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发现无论东西方的历史文化,都存在着对女性做“荡妇”与“圣女”的区分。而划分这一不同形象,甚至塑造某种本质的因素正是性。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在其《性与性格》中指出,当女性被看作无法脱离其自然与生物本性的弱者,而总是耽湎于性时,“性”也便由此成为束缚和压迫她们最重要的手段。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也指出,围绕着男性利益和欲望所建构起的性别制度,在压迫和剥削女性的手段中,性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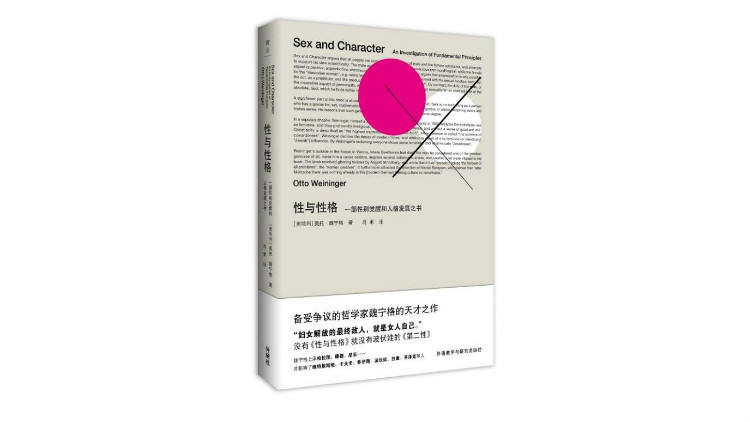
《性与性格》,作者: [奥地利]奥托·魏宁格(Otto Wengier)译者: 肖聿,版本: 雅众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11月
也正因此,看似私人的“性”的背后其实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在鲍毓明与李星星之间,与性连接在一起的诸如性别、年纪、社会地位和身份等范畴的参与,让这一性侵本身变得更加复杂,且也由此折射出奉行着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来评论此事的无论是网友、地方执法部门(如李星星一开始报警的烟台派出所),以及媒体和社会,都显露出某种肤浅甚至无知的趋向,也由此导致人们开始关注和反思当我们讨论涉及性/别的诸多犯罪行为时,我们自身潜意识中所存在的各种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也在阻碍着真相和正义的实现,而“完美受害者”便是其中之一。
当人们讨论在#MeToo运动以及其后所爆出的诸多涉及性骚扰和性侵案件时,许多人以某种看似“理性”和“法律逻辑”的立场来质疑众多受害者女性的一言一行。这看似可以理解的行为背后,其实忽略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社会本身在性/别问题上先天的缺陷。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而这一点甚至不仅仅只体现在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条文中(从恩格斯、倍倍尔到麦金农,他们都发现在那些看似建立在普遍性上的制度和法律中,其实暗含着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同时也渗入在我们的传统、日常行为和观念以及“心灵”之中,即内化了这一性别意识形态,从而认为其具有某种自然的先天性,而忽略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被压制、驱逐和剥削的个体和群体的欲求。
2
完美受害者:
一个不可能的“标准”
无论是对只有14岁的李星星,还是其他成年女性而言,当她们遭到性骚扰和性侵时,首先遭遇的是一种“他者”——以男性欲求和利益为中心的性别制度——的规范和话语。因而导致她们一方面常常无法“理性”地、有“逻辑”和条理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另一方面也往往让倾听者——尤其当他们是男性时——无法理解。当李星星报案面对男性警察时,后者一方面根据相关有限的线索判断并无性侵发生,但与此同时他也难以“真正地”理解女孩所遭遇的处境和心理。最终出现的,便是我们在音频中所听到的淡漠和厌烦。
正是在无法“理性”的言说自己遭遇的状态中,受害者女性遭遇被怀疑的同时,也被性/别制度抓到把柄。因此我们也会发现,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其实便是后者所设置的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让那些遭遇性骚扰和性侵的女性们难以企及,从而质疑其遭遇、话语和品质。于是第二次污名开启,让受害者彻底失去“诚信”,让她们只能继续躲在黑暗中。这个过程最终产生的威吓与污名再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强制内化进男男女女的心中,最终导致受害者开始自我谴责和厌恶,而为了脱离这一困境,最终只能寻找各种有限的方法来说服或拯救自己。因此,我们才会时常看到诸如李星星或是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所使用的方法,即学着“爱上”施暴者。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 林奕含,版本: 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正是这一“爱”,让许多人认为自己发现了受害者的“破绽”,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质疑受害者的诚实,而忽略了导致这一扭曲背后的真正动因。这也让围绕着性骚扰和性侵的讨论呈现出某种微妙,并产生了鸿沟。
而性别差异或许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男女有别”这一规范不仅仅只是男权性别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它也渗透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学校和工作等诸多社会领域中。在看似平等的教育和希求背后所遮蔽的,是如今变得更加温和且不易察觉的性别区隔。赵南柱在其《82年生的金智英》中便向我们展现了同一家庭的男孩女孩在成长、教育和工作中可能遭遇的种种差别对待。这一差别最终造成的并非有自我意识的选择,而是某种刻板印象下的等级,并且当这些意识形态和观念与日常的个体经验相结合后,我们便会发现作为性别制度场域中核心地位的男性,往往缺乏甚至是下意识地忽略女性的差异和感受。而当他们意识到某些差异时,又往往总是内含着诸多贬义色彩,如传统中认为女性缺乏理性、逻辑思考能力,比较情绪化等。
正是在这样的差异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女性遭遇性骚扰和性侵犯时,许多男性的冷漠、质疑、嘲讽和傲慢。在其背后所体现的既是现代最基本的性别意识的匮乏,也是对于他人遭遇不幸时失去了某种本应该超越诸如性别、种族和地域等有限范畴的感同身受的能力。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作者: Laura Mulvey,版本: Palgrave Macmillan,2009年4月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作者: Laura Mulvey,版本: Palgrave Macmillan,2009年4月
当我们看到各种文章或批评、或义正言辞地要求“完美受害者”而忽略了性犯罪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时,我们发现他们所产生的、认同的往往是作为男性的施害者。这仿佛就是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者劳拉·穆尔维在讨论电影中的“凝视”(gaze)时所发现的现象,即作为观众的男性往往通过与屏幕上的男主角产生认同,来凝视和消费女性。在此,女性成为某种被动的客体,承载着前者的想象甚至意淫。
3
法律是最后的底线,
却并非一定能呈现真相
这一模式我们在许多报道此次鲍毓明事件的新闻中都能察觉一二,即其中充满了男性的窥视欲以及由此所想象和建构出的一幅活色春香之图,满足了男性社会的连接与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当许多评论者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来比附鲍毓明与李星星之间的关系时,背后显露出的不正是这样一种男性的集体看似“无意识”的欲望的诡辩?
而遭遇着性侵犯的女性也再次成为男性想象和意淫中的受害者,从而也就削弱了人们对于性犯罪的重视和真实性的肯定。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诸多性骚扰甚至性侵犯而毫无意识时,这不仅仅只是性教育的缺失所致,也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性/别制度本身所赖以支撑其运作的男性群体的“隐秘”联结手段。

《洛丽塔》,作者: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者: 主万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12月
根据媒体报道,鲍毓明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以及因其律师身份而关注过性侵女性的法律问题。当此事曝光,人们在惊讶的同时也只是认为他再次验证了那个颇为古老的情节,即“男性+钱+权+色”的陈词滥调。当福柯讨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经验时,他便指出,伴随着人们对性的关注越来越多,性开始被各种规范和权力掌控的状况也就越来越主流。
然而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只出现在现代,就如列维-施特劳斯在讨论人类原始的亲属结构和权力模式时便已经发现,女性与其(能够进行人的再生产的)性资源可以成为流通和交换的货币。对女性与其性的掌控,便是性别、权势和身份的象征。当一些媒体揭露出存在于当下社会中一些有权有势的男性通过“领养幼女”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时,这一看似古老的恶行也依旧无声无息地蔓延至今。
李星星曾两次报案,但都被以证据不足而撤销。就如许多报道所发现的,由于鲍毓明本身的法律知识以及其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使其有一套完整的说词来面对法律的调查。而也正是他的这一自信,让许多人宣称只有遵循法律的程序才能评判鲍毓明的行为。然而就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原本就受制于社会性别制度的法律或许难以真正地弄明白女性在此类事件中的遭遇,许多无法被“理性”和“逻辑”地言说的感觉、羞愧、恐惧和无奈也因此被排除。这很可能让法律最终难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的(著名导演波兰斯基的逃脱,不正是最典型的案例?)。除此之外,法律是社会的最后底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能作为判断一件事情最合适的标准。
围绕着此次鲍毓明案件所形成的各种观点,其实也展现着当下我们自身对于性/别的意识与反思程度。在各种看似微妙甚至撕裂的对立中,我们都受制于其中,一方面是为其所教育和规训的性别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言说和实践,或巩固旧有的规则,或批判甚至推翻以重建新的规则。
当我们要求遭受着性骚扰和性侵犯与强奸的女性(以及男性)拿出足够的证据、保持着某种完美的受害者形象时,与其说是为了真相或正义,不如说其实依旧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制度的险恶手段。“完美受害者”的悖论本身就是新的污名和伤害,面对它,有限的个体始终是被压迫者。
在这个如此不完美的世界和社会中,一方面作为建造着、维护着这样不完美状况的主流群体,另一方面收获着性别红利的既得利益者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存在着“完美的受害者”呢?
作者|重木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