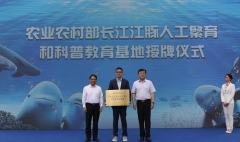七月的暴雨,让鄱阳湖流域的诸多村庄围困于洪水之中。而湖面下的江豚也面临着危险。
在鄱阳湖,江豚拥有一个更本土化的名字——“江猪”, 生活在鄱阳湖的江豚数量占整个长江流域的一半。它被看作是这个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生态体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示物。
时隔三十年,鄱阳县江豚巡护队队员范细才又一次在鄱阳湖白沙洲水域看见江豚出没。那是2019年的4月,平静的湖面一开始只显现出小鱼群聚集形成的水花,没过多久,七八头江豚陆续从湖面交错跃出。

今年4月,巡护队员在鄱阳湖龙口水域观察到江豚身影。图源受访者
40公里外的龙口水域,范细才的同事毛国启,在5月初见证了一次更壮观的江豚出水。队员们用手机记录下这个画面:一头接一头的江豚接次腾出水面,毛国启的欢呼声盖过了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他们特意数了一下——有五十多头江豚。
这支成立于2018年的六人江豚巡护队,除了队长,其余队员均由湖岸边的渔民转型加入。在过去一些年里,鄱阳湖经历了猖獗的非法捕捞,原本平衡的湖面生态被打破,江豚数量骤减。
2020年以来,鄱阳湖最严禁捕令颁布,范细才、毛国启等人从捕渔者到护豚员,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水上。
洪水退去,护豚队出台“悬赏令”
对鄱阳县江豚巡护队的成员来说,今年夏天的汛情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工作内容。过去,队员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观测记载江豚的种族数量和活动规律。
但洪水来了,清运湖面垃圾成为最耗时耗力的一项。“树枝、泡沫、塑料瓶、废弃渔网,陆地上有的垃圾湖里都有。”白沙洲水域的巡护队员范细才说。今年汛期南风一吹,垃圾便被带到湖岔众多的白沙洲。数量最多的时候,一条载重10吨的巡护渔船,可以在一天之内清运两三百公斤的湖面垃圾。
7月9日,巡护队的船在鄱阳湖上熄了火,停在湖中央一根竖立的长竹竿旁。队员毛国启和弟弟毛国平穿着橙色的救生衣,三五下便合力把竹竿底部纠缠的障碍物拽出水面——那是一张废弃发黄的渔网,边缘一侧装满小石子,是过去捕鱼人为了让渔网沉到深处而特别设置。
江豚巡护队的队长蒋礼义说,这些湖面垃圾中,废弃渔网对江豚的伤害最为直接。“因为如果不及时打捞,一旦江豚误入废弃渔网,它被缠住了就会受伤甚至死亡。”

7月20号,巡护队员在鄱阳湖巡查时打捞水中的废弃渔网。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湖中清理出的带着石头的渔网,是过去渔民遗留在湖中的废弃物。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环保项目总监钱正义,从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就读博士期间,便一直从事江豚种群的研究。他担心,洪水暴涨后江豚至少面临三方面的环境影响——水域面积扩大后,江豚有机会游到以前到不了的浅水位区域,一旦退水,江豚可能面临搁浅的风险;鄱阳湖的渔业资源相对恒定,水域变宽后,以长条鱼和小鲫鱼为生的江豚,在捕食鱼类时增加了难度;另外,涨水期间会有人用锚钩钓鱼,也可能会在无意之中误伤江豚。
7月9日,江豚巡护队监测到鄱阳湖龙口水域的湖面上出现9艘不明船只。“还以为是有人冒着风雨和禁捕令偷偷下湖捕鱼。”队长蒋礼义说,等到大家开船靠近后才发现,原来是上涨的鄱阳湖水位把隔壁余干县的9艘渔船冲进了鄱阳县水域。
事实上,洪水对江豚带来的生存影响还没开始完全显现,退水之后,才是真正的危险和挑战所在。蒋礼义2012年3月曾参与过营救搁浅江豚的行动,当年同样赶上洪水,3只江豚在饶河支流的乐安河水域搁浅。
抵达现场后,他与同事一道用快艇、渔船将困在小圩堤内的江豚转运到深水区。救护过程小心细致:担心坚硬的船体划伤江豚,救援人员提前铺上了软垫;江豚皮肤光滑娇嫩,出水后要不停地给它浇水,浇水动作要持续、轻缓,还要注意不能将水灌进江豚头部两侧的呼吸孔里。
也就是那时,趴在江豚身旁照顾的蒋礼义,头一次近距离听到江豚从气孔发出的声音,“呼、呼、呼。”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玉江博士表示,目前长江流域设立了一些江豚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把江豚从长江里面捕捞起来,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区域。这些区域对洪水更敏感一些,水位也会跟着上涨,有可能造成江豚逃逸。
“如果江豚逃逸后没有游入长江,而是冲到了农田里的浅水区,水退后出不来就会在里面死亡。洪水还有可能夹杂一些泥沙、石块、树枝杂物,可能会造成威胁。”郝玉江说,要在溃口区域或是行洪区做好江豚搜救工作,发现后及时救助。
靠着那年营救攒下的经验,今年汛情来临后,鄱阳湖江豚巡护队便出台了一则“悬赏令”,鼓励流域内的沿岸村民,如果在退水后发现受困、搁浅、受伤江豚,及时报告至江豚保护协会,将给予800至1000元的奖励。
“这或许是调动当地村民参与搁浅江豚营救一个最直接的办法,”蒋礼义认为,“鄱阳湖这么大,我们巡护队不可能每个角落都能照顾得到,就鼓励大家来加强监测。”

在鄱阳湖面巡护时,船尾的发动机螺旋桨时常被缠住,需要用刀割开。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江豚狂人”
这支江豚协助巡护队成立于2018年。除了队长蒋礼义,其余5名队员均为土生土长的渔民。
在鄱阳县的水生动物圈子,蒋礼义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老蒋1米七几的个子,留着短短的平头,脸型略方。只有在谈到他和队员做江豚保护的工作时,他会提高声调比划手势,笑得眼角都挤出深深的几道纹路。
朋友们总觉得他是个“江豚狂人”,朋友圈里转发的几乎都是和江豚保护有关的信息,连他的头像都是一张穿着保护江豚标语的绿色马甲照。他乐于向身边的人讲述和江豚有关的事,有时候家人听他念叨多了,小儿子也朝他抱怨几句,“哎呀爸爸,你能不能别一天天都是江豚江豚的。”
别人问他为什么对江豚这么感兴趣,他说不出具体原因,只记得从小就对这种被当地人称作“江猪”的水生动物充满好奇。不到10岁的时候,他跑到当船员的父亲船上去过暑假,看着水里“黑黑的东西”一拱一拱地跟着船跑,“老一辈的人把江豚说得比较神秘,说它有灵性,如果你(开船的人)对它不好,它们就会把你的船拱翻。”
在航运公司工作到41岁那年后,老蒋所在的企业改制,他被当时的渔政局聘请为编外人员,慢慢接触到水生生物保护的领域,并得到了彼时鄱阳县渔政局的支持,成立了鄱阳湖流域首家江豚保护协会。
老蒋招募巡护队员要求颇高:渔村村民大多世代相熟,人情交往复杂。巡护队员必须得是地道的渔民出身,对当地水域地形、捕捞工具都非常熟悉,人缘好威信高,在村里说话办事能管用。
那一年,原本是渔民的范细才和范海华看到老蒋招募队员的信息,便主动报名,“我们从小是打渔的,对江豚是有感情的。”加入巡护队,意味着要上交自己的捕鱼证,不能再以此为生,一些队员还低价出售了自己的渔船。
在范细才的记忆中,自从小时候会走路,他便开始跟着爷爷爸爸的船到湖面玩。正式下湖打渔的那年,他也不过12岁。

从左至右依次为队员范海华、队长蒋礼义、队员范细才。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在鄱阳湖里踏着浪涌翻滚了30年。“我的人生全部都是在这里,梦想也好什么也好,我的思想就在这里,除了打渔还是打渔。”范细才记得,村里资历最老的渔民,从十几岁上船到70来岁下船,一辈子只会“搞鱼”,他祖辈长居的车门村有着700多年的打渔史,直到千禧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离家到外地务工的年轻人。
过去,每年3月20号至6月20号是禁渔期,鄱阳湖的渔船熄了火,为各种鱼类产卵留下空间。从5月开始到11月的半年里,则是渔民最繁忙辛劳的时间。同靠一片湖,每个村捕捞的水产并不相同。
范细才所在的车门村,渔民大多捕捞虾和银鱼。一斤晒干的大银鱼能卖到800元。水大鱼多的年头,一个渔民家庭半年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0来万元,勤快些的人家,会在鄱阳湖的枯水期前往安徽、湖北等地帮人打渔,最高一个月能带回几万块钱。
但有些渔民为了赚更多的钱,在禁渔期偷捕或是进入禁止捕鱼的保护区,还用上极具破坏力的电网、迷魂阵、吸螺机、绝户网等极端捕鱼工具。原本平衡的湖面生态被打破。
“湖上非法捕捞最猖獗的时候,百分之八九十的渔民都会用这些”,范细才介绍, 捕捞工具中的“绝户网”,一张网长度能达1500米,深度有7米,下网之后,“不管是大鱼、小鱼,都能一网打尽, 一次最多能打捞40万斤”。
对于江豚来说,绝户网的打渔手法,会把原本留给江豚的天然饵料也捕捞到人类的餐桌上,江豚无鱼可吃只能活活饿死。在2019年下半年的枯水期,鄱阳湖水位较低,江豚觅食困难。鄱阳县农业农村局的渔政部门与巡护队员一起购买了将近4000公斤活体长条鱼,投放至江豚活动的区域去。
渐渐地,鄱阳湖上过去常见的鳗鱼、河豚、江豚,在非法捕捞猖獗的那些年再也难觅踪迹。队员朱合文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早一点到外面去创业,“照这个样子打渔,湖里的鱼迟早要打光的。”

为了让巡护船和普通红色渔船区别开,队员们自己给船刷上蓝色油漆。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从“ 捕鱼人”到“护豚人”
范细才们在正式成为巡护队队员之前,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内容包括江豚种群的基本知识、搁浅江豚的救护以及每日巡护APP的登记使用。这些四五十岁的男人们不但要走下渔船,还要学习使用手机拍摄视频宣传江豚保护。

2019年4月,在湖面发现江豚踪影,巡护队员举起手机拍摄记录。图源受访者
鄱阳巡护队分为101、102两个协助巡护小队,分别在龙口至瓢山、白沙洲至八字脑水域开展巡护,单向巡护距离达40公里,辐射鄱阳县辖区的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和鄱阳湖鲤鲫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
近三年时间里,6名队员每天在湖面巡护3至4小时,累计巡护里程已经超过4万公里。
监测江豚的出没是巡护队首要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这种铅灰色的哺乳动物都在水下活动,偶尔会跃到水面呼吸和觅食,每次出水在三秒左右,重复三五次。不同于鱼类尾部的左右摆动,江豚尾部的上下摆动会形成特有的水花形状。
队员们便要学会识别江豚出没的迹象。有时候,在靠近湖面的地方如果有海鸥出现,也不排除江豚活动的轨迹——因为大多数江豚都是三五只一起,把鱼围赶到一堆方便觅食,海鸥也在此时顺带进食。
成为江豚协助巡护队员后的第一年,范细才也没怎么见到江豚。他对江豚的好感来自幼年时——自家的船在行驶时,江豚会在旁伴游,总跟船保持一定的距离。“江豚通人性”,记忆中的“江猪”常见,最多的时候,一次能见上百头。
范细才成年后,能看见江豚的次数越来越少。“据2012年、2017年两次比较全面的调查统计,长江流域大概有1000余头江豚,其中450头左右生活在鄱阳湖流域,”钱正义说,最近的一次民间NGO组织的数据预估,鄱阳湖的江豚数量大约在500头左右。
平时的巡护过程,每行驶到江豚常出现的地点时,队员们都会习惯性地举起手机,对着江面,希望铅灰色的身体能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队长蒋礼义最希望见到的是“小豚”,“有小豚我就相当高兴,小豚出现,就说明它们在繁育下一代”。
“急性子”也被逼成了“慢性子”
除了和江豚打交道,巡护队队员们更多的时间需要和渔民们“交手”。每年的3月20日至6月20日是鄱阳湖的春季禁渔期,禁渔区内也禁止一切捕捞、收购、贩卖水产品活动。打击非法捕捞成了巡护队员日常工作的重头。
过往渔民的经验现在派上了用场。巡护队员们看见四艘船组队,同时拖动一张渔网在湖面作业,便明白大概率是“绝户网”;如果船舱里摆着巨大的吸螺机,船尾两根绳分系着两张渔网,那很有可能就是“吸螺船”。
巡护队要做的就是“拍照留证据警告,把道理讲清”。他们没有执法权,更多是配合渔政做协助工作。“碰上不听劝告的,就打渔政电话协助,不能吼”。这些过去的强势的老渔民们现在成了打击非法捕捞的巡护队,“急性子”也被逼成了“慢性子”。
2019年,在101巡护队所在的龙口水域,三名巡护队员为劝离在保护区捕鱼的老夫妇过程中,两船僵持半小时。
老人使用鸬鹚捕鱼,这是一种传统的捕鱼方式。专业养殖的鸬鹚在渔夫的指令下,将捕获的鱼衔入船舱中。巡护队在保护区发现这艘船只的时候,夫妇一人手握竹竿,一人驾船,分别站在木船两头。木船两侧的木棍上,整齐排布着二十多只鸬鹚,老人手握竹竿将脚上拴着绳子鸬鹚驱赶下船捕鱼。木船的活水舱里,有老人此行收获的十几公斤鱼。

禁湖之前,湖面上会有年纪较大的渔民使用鸬鹚这样比较古老的捕鱼方式。受访者供图
巡护队告诫之后,两位老人仍以捕鱼工具合法为由,不愿离开保护区。小木船和巡护队的铁船在浅水区绕圈周旋。“好话说尽,嗓子都喊哑了”。最后小船被逼上岸,交由渔政处理。
从捕鱼者成为护豚人,巡护队队员们协助打击的非法捕捞的对象,大多是同村的渔民。在世代捕鱼的村庄,他们站到乡邻的对立面,也招致不少非议。
“你不让我们捕鱼,我们吃些什么?”,制止村民在保护区捕捞时,有村民反驳;也有更直接的奚落,“不要拿江豚这套来吓唬我,你做的这些事是我不愿干的,你一个月赚的3千元,不如我一天赚的多”;工作之余,看见亲戚邻居话家常,聊得热络,范细才一加入,话题就中止了;甚至在队伍出船巡护之际,发动机故障无法发动,检修之后发现被人故意拔了汽油管……
队长蒋礼义只能不断跟队员做心理建设:“上了这条船是没有回头草吃的,否则渔民是会笑话我们的,所以再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隔了30年,我终于又看到江豚了”
但最近,不止一位熟人托范细才打听,“能不能跟你领导队长讲一下,还能不能进队伍?”这些人中,就有当初对他恶语相加的乡邻。
为保护鄱阳湖区生物资源,2021年1月1日起,江西省将全面禁止鄱阳湖区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禁捕期暂定10年。其中对于列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的水生生物保护区和长江干流江西段,2020年1月1日起禁捕。
自禁捕以来,鄱阳县数万渔民都面临转产转业。直接找到队长蒋礼义打听这份差事的人也不少,有陌生干部发来短信问“给巡护队伍增加人员的事情”,也有通过自己老家亲戚朋友打听的:你们这里搞了一个巡护队,还要不要增加人?
范细才说,往年这时,鄱阳湖涨水是渔民的丰收季,湖上生活热闹异常。捕鱼工作完成后,大家把十来艘船用绳子并排固定在一起,渔民们在夜色中“打拼火”,一起买菜做饭。晚间,鄱阳湖的水面喧闹欢腾,最多时能汇集近千艘渔船同时开捕。探照灯打开,发动机齐响,湖里“呜呜哐哐”地震动,宛如水中“夜上海”。
当捕鱼不再是生计,范细才的村子里,过去的渔民都陆续走出村子,“男人做泥工、打零工,女人则大多进了厂”。全面禁捕后的鄱阳湖,如今湖面除了巡护船、渔政船和货运船,再也见不到其他船,湖面“空落落了很多”。

过去鄱阳湖渔民用丝网捕鱼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但这两年,江豚的数量明显在增长。巡护队队员们越来越频繁地在鄱阳湖与江豚相遇。
钱正义认为,在鄱阳湖的生态系统中,江豚是其食物链中处于顶端的指示物种。“也就是说,除了人类,江豚在这里没有天敌,在整个生态系统来说,这是具有指示意义的。简单讲,如果江豚的数量多,那就说明鄱阳湖的生态系统好,江豚的数量少,则意味着生态系统糟糕。江豚的数量,最有效直接地反映整个鄱阳湖的健康状态。”
钱正义对鄱阳湖的生态改善持乐观态度,“非法捕捞减少,鄱阳湖的渔业资源比较丰富、非法采砂等也得到有效控制,按照现有态势发展,江豚数量增长是指日可见的。”
当范细才在白沙洲水域看到江豚的铅灰色踪迹时,他兴奋告知队长,“我惊呼啊,高兴啊!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看到江豚,隔了30年,四十多岁的时候,我终于又看到江豚了!”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魏芙蓉 实习生 汪子芮 李雨凝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