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罗拉 段雅馨
骆以军是个会讲故事的人。
读骆以军的小说,你可能觉得云里雾里,但听他讲故事时很难不被吸引。再琐碎的小事,配上他生动的描述和丰富的动作,都变得有趣形象了。最后,那些关于创伤与救赎、异化与孤独的主题,在幽默表达的缝隙里缓慢流淌出来。
骆以军快到40岁才开始写小说,因狂暴的想象和华丽的语言脱颖而出,迅速成为台湾中生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最经典的《西夏旅馆》《女儿》都以萎靡、奇诡而出名,今年又出版了《匡超人》。这本书从《西游记》的美猴王写到《儒林外史》的匡超人,瑰丽的想象依旧扑面而来,是骆以军自己都觉得“写得非常好看”的小说。(《匡超人》获得了2020年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设的红楼梦奖决审团奖)
7月22日,骆以军带着《匡超人》做客新京报·文化云客厅直播间,一个小时的直播,他从关于变形的三个故事说起,聊到美猴王如何作为他精神世界的引领,以及为何用《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命名此书,让人大笑的同时也更理解了书中那些仿佛梦境般的呓语,感受到骆以军如何“在这本小说里动用所有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的感觉或技术,来翻滚展现世界的不断变形。”

骆以军,作家,一九六七年生,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艺术学院(现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研究所毕业,台湾中生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曾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首奖、第五届联合报文学大奖、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台北文学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项。
写小说的人,需要像尊菩萨,
承受所有的苦厄
骆以军成长于台北旁边一个叫作永和的小镇。“我那一代人眼界的开放、接收的爆炸性信息全部得益于西方的现代小说。”从18岁到48岁,他说自己很扎实地阅读了福克纳、卡夫卡、川端康成、杜思妥也夫斯基,一路读到奈波尔、石黑一雄和印度、拉美、东欧一些比较冷门的小说家,最后读到波拉尼奥。“老实说我根本没去过俄罗斯、莫斯科,可是当我20多岁在阳明山的小树林里抄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西方20世纪小说家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瘟疫,以及强权之间的恐吓和人心惶惶的恐惧。”
早年这种大量阅读灾难的经验甚至让人患病。2016年前后,骆以军病了很长时间,一度患上心肌梗塞,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有一天,一个更奇异的病突然降临——他发现自己某个身体部位破了一个洞。
许多跟他同年龄的作家朋友近来也纷纷得了一些怪病。比如他的好友黄锦树得了重症肌无力,董启章生了一种类似恐慌症的怪病,还有很多台湾的同辈小说家甚至走到自杀的地步。“我们的日常活动明明只是写小说,并没有花天酒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骆以军的大学老师杨泽分析,他们这批人从年轻时到现在一直依赖感性经验,对自己所处的文明缺乏足够的理解。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却迅速地吞食西方最纯的文学“海洛因”。这些文学所采用的方法论、表现形式是非常损耗内心的,如果读得太多,读者的内在只能爆掉了。
骆以军选择用更有趣的方式想象这个“洞”——他把它看作《三体》中的外星人在开虫洞时找错了位置,不小心在自己的身体上开的一个框。自己的痛不欲生,其实是在为人类和宇宙之间的连接提供出口,“只要低下头,就可以看到各种小型星际战舰从破洞里开出来。”
更巧的是,如命运安排般,骆以军某天花200块收来一尊金刚菩萨,不经意发现菩萨的脑后也破了一个大洞,他终于顿悟,想到不论是卡夫卡、马尔克斯,还是最残虐的波拉尼奥,世界上所有的小说作者在创作时都保有一个核心的概念——救赎。他告诉自己:“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你需要像这尊菩萨一样,把人世间所有的嫉妒、痛苦、暴力、暗黑、恐惧吸吮到自己的内部,承受所有的苦厄。”

直播中的骆以军
用小说来记录“变形”与“倒置”
骆以军有一次在杭州演讲,应主办方要求,他特别准备了三个关于变形的故事,以应和当地的古老传说《白蛇传》。跟以前在学校、书店里面对文青的演讲不同,那次是在京杭大运河的一艘船上,对着三十几位大爷大妈讲故事。大家坐在桌子前,桌上摆着盖碗茶,外面是湖光山色,一片翠绿,非常悠闲,但船的马达声很大,伴随着水波振动的声音,大爷大妈和孙子说话的声音,他开始讲。
骆以军讲了三个关于变形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他年轻时看过的一部爱斯基摩动画片,《男孩变成熊》,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有一天,一对爱斯基摩夫妇出门后,一只母的北极熊把这对夫妇的小儿子叼走了,这只熊妈妈把小男孩当成自己的小熊崽一样照顾,教他各种维生的技能。另一边,小男孩的亲生父母疯狂地找了十年,直到有一次碰巧射杀了熊妈妈,才发现了小男孩。回到人类的居住地后,小男孩仍然把自己视为熊而不是人类,总是遭到其他孩子的霸凌,以及亲生父亲的规训。小男孩非常痛苦,只好跑去跟山神祷告,想变回熊。山神告诉他,要想变回熊,必须通过三个大自然的考验:第一是跳进海里经受最残酷的洋流的冲击,第二是要承受地表上最猛烈的飓风,第三是要在雪原上忍受最难熬的孤独。经过这三关以后,就可以变回熊。最后,经受了重重考验,在鲸鱼和牦牛的帮助下,小男孩终于变回了熊。
第二个故事来自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说《奥拉》,小说里有一位不愿意变老的老太太,标题里写的年轻女孩奥拉其实是老太太的分身。第三个故事来自骆以军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最初养过一只蝈蝈作为宠物,但只养了6个月就死了。这件事让她很伤心,发誓再也不养寿命比人还短的生物,于是跑去日本定制了一个人形关节,比充气娃娃更逼真,跟真人的大小、触感都很像。
骆以军对着杭州的老头老太太讲完这三个故事,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跑进了一座全部是黑人的教堂里讲白人的笑话,有种说不出的冒犯和尴尬。听众同样非常困惑,反应冷淡,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一大串西方的、科幻的东西。
船行到中途,到达一个折返点,停下来让大家休息。骆以军非常沮丧,跑到船尾去抽烟,这时候有一位老大爷还跑来问他:“你哪来的?你讲话的口吻怎么这么怪,跟周杰伦很像啊!”
但骆以军后来发现,船上的大爷大妈们其实是很有教养的,他们会讲唐诗宋词,知晓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了解宋朝人如何斗茶、如何鉴赏瓷器。可是突然跑来一个怪人,跟他们胡言乱语,大谈男孩变成熊,大谈奥拉,这种场面实在吊诡,很像拉美小说家们常玩的时间幻觉游戏,把极短的时间跟无限的时间相互错置。他感受到其中的变形和扭转,于是把这段经历编成故事,收录进自己的《匡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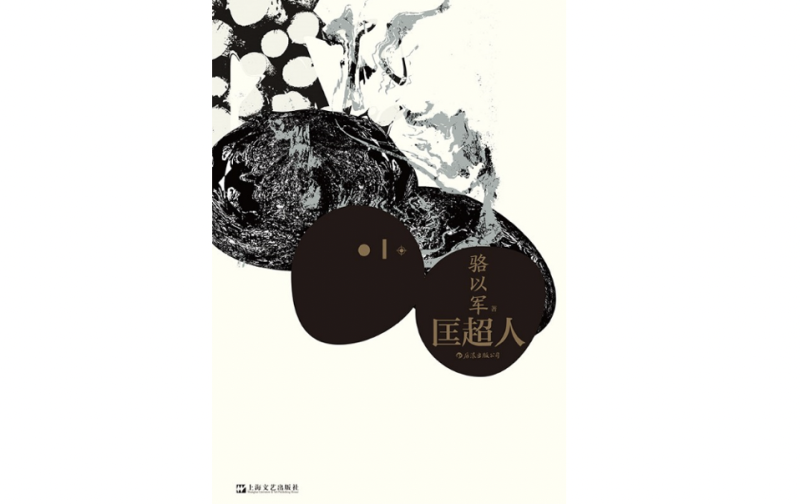
《匡超人》,作者:骆以军,版本:后浪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
倒置、变形是《匡超人》里重要的主题。骆以军的父亲1949年从大陆入台,生活环境彻底改变。仿佛张爱玲的自传性小说《雷峰塔》里谈到她的父母,谈到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代人,就像磨坊里碾盘上面的谷糠,而且是被搁在最上面的谷糠,是第一代被中西文化冲突碾碎的人。
张爱玲的父亲原本是前清贵族,从小要读八股文,但是当他成年后,八股文却被灭掉,那些古老、典雅、笨拙的文字全部消失,所有人都要学习西方,所有人都要进入现代。张爱玲的父亲虽然是前清旧时代的人,但他会读尼采和叔本华的书;他根本没出过国,却会戴配有不同时区钟面的手表,也是最早一批去订做白铁皮的书桌书柜的时髦人士。
那代人经历了内部的变形破裂,他们会怀疑自己究竟是熊还是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遭受的震荡那样延续下来,震荡到张爱玲,震荡到鲁迅,震荡到莫言、王安忆,震荡到100年后的双雪涛、阿乙、张悦然,西方爆破性的力量在100年以来的中国人心里开了一个洞,这个洞造成的伤害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是骆以军想呈现的命题之一:“在《匡超人》里动用所有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的感觉或技术,来翻滚变化,展现世界如何不断变形。”
《儒林外史》里写的偷拐抢骗,
已比索尔·贝娄更通透
美猴王之所以能成为《匡超人》非常重要的驱动引擎,是因为他带来两个话题:“变形记”“西游记”。孙悟空一直有办法变貌,可是他的变形却是因为如来佛、观音菩萨一路的镇压。就好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一系列磨难,一路让清朝人“变乖”,甚至后来清朝人追求全面西化,仿佛那只拼命要变成熊的男孩。
对骆以军来说,美猴王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引领。“刘再复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里只有两个人物至臻纯美。这两个人物一个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的灵魂太纯真了,面对这个暗黑、粗暴的世界,她宁愿折断,也还是那么‘叽歪’——不是‘叽歪’——还是那么不会妥协,不会稍微嘴甜一点,稍微虚与委蛇一点,讨好一下姥姥,拍一下下人马屁。她不会,她就折断了。另外一个至臻纯美的人物是《西游记》里的美猴王,作为一只猴,他根本不管仙界、玉皇大帝那一套秩序、伦理,他只管捣蛋、破坏、翻天搅地,在没有电影的时代,美猴王的变形记足够让你目眩神迷。后来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一系列的IP改编,美猴王永远是票房灵丹,所以我们整个民族对美猴王一直有一种理解跟共振。”
这也是骆以军在《匡超人》想实现的愿望:“我希望我在小说里重新再造出一个水帘洞,留住我梦幻中的美猴王。《西游记》最美的开头就是孙猴子和小猴们在花果山水帘洞嬉戏、翻滚,跃过瀑布,里面有石桌石椅,就像‘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个苏东坡他们最喜欢的山水画世界。”
《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是另一个关于变形的故事。最后选他作为新书的名字,也是因为骆以军十分佩服《儒林外史》这本小说:“它就像皮影戏,那些人都没有具体的面貌,没有西方小说里的复杂的描述,人在各章节只是讲一些废话,像傀儡一样。 ”
匡超人,原本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少年。他坚守着心中的价值,对未来充满想象力,但等过了十几个章节他又出现时,因为吸收了太多江湖的污秽,他变成了一个虚与委蛇的小人。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研究者商伟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的是18世纪明朝中晚期之后,中国士大夫心灵跟话语之间的背离。商伟说,从春秋战国到汉唐宋,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掌握的话语体系已经过于熟烂和僵化。在这套话语体系里,士大夫们明明知道那些陈词滥调是僵死的,可依旧像AI一样不经思考地输出这种语言。
“所以我说,明朝《儒林外史》写人心灵的偷拐抢骗,就已经比索尔·贝娄写的《洪堡的礼物》里更通透。我年轻的时候都在读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这几年重看中国古典的小说,比如说《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我会感到一股非常强的暗流。好像书里的许多人不知道在干嘛,整天吃饭喝酒讲空话,其实他们把该办的事情都办了,他们该交涉的权力关系、师生关系、情感关系,以及官场里面的整套秩序利益,全部有一套非常平稳的话语系统在里头运转。”
这可以和看鉴宝节目的乐趣联系到一起。骆以军一度迷上了大陆的鉴宝节目,“南昌寻宝”“安徽寻宝”“深圳寻宝”......甚至常常看到深夜,取代了曾经唯一的熬夜方式看小说。鉴宝的精髓在于判断宝物是真是假。总有人强于作假,也总有人要拆穿这种假,看宝物作伪和辨伪之间的厮杀,便成为观众的乐趣所在。
骆以军总结出,这种热衷于辨伪的乐趣,是从古一脉相承的。“我们的民族文明像锦绣一样灿烂,但如果你以小说的方式去观看人类形态,会发现其实我们消耗极大,甚至最大的精力,就在辨伪。比如孙悟空有真假美猴王,连观音都分辨不出来,还常常用各种偷拐抢骗的伎俩,他是最会用这种《儒林外史》里这套假把戏的人。”
人们总是透过说故事去判定自身大量的故事或伪故事,在分辨真伪时消耗了大部分精力或全部精力之所在,到底如何判断真伪?分辨真假有那么重要吗?或是说创造力的核心到底需要放在哪里?这本《匡超人》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找到答案的可能,正如骆以军所说:“通过这本书我希望大家出现一个画面,在一个空旷的平原上,一端站着美猴王,另一端站着匡超人,他们两个在互相朝对方走去。 ”
新京报文化云客厅——云享文化生活,live每周不停
更多直播活动,欢迎关注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文化客厅微信、新京报APP文化频道、新京报书评周刊微博活动预告
撰文|罗拉 段雅馨
编辑|吕婉婷 李永博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