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将《文城》的历史背景设定为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发生地则是一座并不存在的南方小城。北方青年林祥福与南来女子小美相遇、相爱,但小美在生下一女儿后突然离开,再无音讯,林祥福背着女儿一路南下,寻找妻子小美所在的“文城”。这一寻就是一生。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中国当代作家,著有《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图为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020)中的余华画面。
《文城》在2月22日刚一面世就引起市场关注。首印50万册,并在预售次日加印10万册。在当今中国,这是纯文学写作极其罕见的数据。除了惊人的销量,《文城》在内容上也得到诸多赞誉,在这其中,更有作家同行、文学批评家和书评人将其视为余华的重返巅峰之作。而这巅峰,便是《活着》。当然,在热捧之外也有与此截然相反的评价。
有人嘲讽“中年风”“老气横秋”“卖惨”“就这”,也有人质疑在城市化率如此高的今天何以不写城市故事,他们中甚至有声音质疑“都什么年代了”还选择一个不入流的旧时代。

豆瓣上的读者吐槽。
我们显然也可以说,大可不必严肃对待这些评价,因为确实也难以否定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让人诟病的“饭圈”逻辑,算不得任何意义上的小说评论。作家本人应是创作的决定者,他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背景、进行什么样的创作。可是,故事、语言或人物却是不得不接受他人评价的。我们推送的本篇评论便是另一种声音。作者思郁并不赞同《文城》是重返巅峰之作这一说法,“比《第七天》好一些,但仍然很平庸”,在他看来,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只不过是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塞进了几个人物,故事老套,人性单一。而这当中的写作技法在《文城》之前已经出现。
当然,如果你刚好也在读《文城》,我们欢迎你在文末评论留言,写出你的看法。
撰文丨思郁

《文城》,余华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1年3月。
01
如果说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有几位的写作能够让人充满期待,其中一定有余华。这倒不是鼓吹余华的写作一直都很厉害,而是说,我们回顾他的写作历程就会发现,他走了一条非常聪明的创作路线。
早期以先锋写作在文坛引人注目,让众多批评家击节赞叹,中期舍弃充满探索性和实验性的写作,回归传统现实主义风格,以《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为代表作,深得大众欢迎,奠定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好感,在市场上也赢得了瞩目成绩。现在我们想到了余华,提到最多的就是《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这两本书被翻译最多,流传最广,也为余华赢得了国际声誉,同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长销书。大概就是从此之后,余华开始意识到了他不单单是一个小众的纯文学作家,还可以是一个成就百万销量的畅销书作家。2005年和2006年《兄弟》,分上下两册隔年出版,算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赚足了眼球,但是这种过于赤裸的市场营销,也损害了文学的完整性,对作家自身的声誉也造成了贬损。此后的余华,真正迈入了百万销量的纯文学作家,《第七天》也好,刚出版的《文城》也好,预售期间,首印几十万本已经告罄,像这种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国内几乎没有一个写纯文学的作家可以比肩。

《活着》的早期版本(左,长江文艺出版社;右,南海出版公司)封面。
但是相对于余华在市场上的成功,他近些年作品的口碑并不能尽如人意。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他早期的作品非常干净、利落、锋利,而且叙事有种不动声色地残忍,从《兄弟》开始,他的写作日渐粗鄙化,就好像一个暴发户,再也不吝惜自己的语言,恣意而放纵。
《第七天》这本小说最让人诧异之处,是它彰显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巨大退步,我们很难理解,像余华这样的作家,竟然没有能力把众多社会新闻进行艺术化的处理,最终呈现出来一种不伦不类的成果,《第七天》更像是一本习作,而不是代表作。
至于刚刚出版的《文城》,有人吹嘘说,这是余华的重回巅峰之作。明显是痴人说梦,巅峰不是你说回就能回的。大多数作家一生都只有一个时期的巅峰,最多也只能有一两本代表作,从此之后会慢慢走下坡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城》只证明余华还可以写作,还具备巨大的市场号召力,这就足够了。至于说《文城》写得有多好,可能比《第七天》好一些,但是依然掩饰不住一种巨大的平庸。
02
《文城》的平庸首先表现在叙事的平庸性。
我们可以把《文城》当成一个爱情传奇,这个传奇的框架里,我们轻易可以察觉出民间传说里的几个爱情故事的影响。比如主人公林祥福抱着小女儿千里寻妻,从北方来到南方的溪镇,堪比孟姜女千里寻夫,可见其用情之深。尽管他不知道溪镇是否就是妻子小美口中的文城,但是凭借模糊的乡音,他最终选择在此处安家落户,扎地生根,这种小概率事件只有用传奇性可以解释。在后续的故事中,童养媳小美与阿强的爱情是另一个版本的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故事,小美被公婆嫌弃,阿强被迫休妻,但他并没有妥协,选择了另外一种反抗方式,跟小美逃离了家乡,这个故事变成了新时代的《孔雀东南飞》。两人以兄妹的名义北上进京,中途被困,小美二次嫁给了林祥福,为其生下女儿,又因忘不了跟丈夫阿强约定,悄然离去。这是中国式爱情悲剧的起因,一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这些古老而腐朽的观念束缚着小美,折磨着她心灵,从此她的灵魂再也无法安宁。小美和阿强在暴雪过后,冻死在祭天的拜祭仪式上,他们的自我赎罪,是中国民间传说中几乎所有爱情故事的必然结局。
但是中国式的悲剧总会弱化悲剧性,渲染传奇性。比如,林祥福多年后死于土匪暴乱,几个仆人送他北上归乡安葬,中途中歇息,林祥福的灵柩正好在小美和阿强的坟墓旁边停留。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另一版本,心诚则灵,林祥福寻妻多年,至少要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就是让他们用一种传奇的方式遇见,生不能团聚,死也要相遇。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020)中的余华画面。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文城》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为了赋予这个故事一种传奇性,就需要在叙事的框架内增添很多故事性,所谓乱世才能出传奇。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文城》里的另外一种传统叙事,把林祥福千里寻妻的故事变成一个混乱时代的小人物在溪镇安家落户,保卫家园的故事。我一直强调余华写作的平庸性,很大程度跟这个部分的叙事有关,如果说《文城》里的爱情故事套用了传奇故事的框架,已经显得过于陈旧了,他在安排和讲述大时代的叙事时,更加捉襟见肘,暴露了掌控能力上的不足。
03
如果我们了解余华的作品,就该知道他最擅长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在每个篇章里尽力刻画个体人物的角色,揣摩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擅长渲染人物群像,尤其是那些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一旦将这些鲜活的人物放置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之中,那些原本鲜活的面貌都开始变得僵硬和可疑起来。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你读过的余华的小说中,能记住的人物有几个,尤其是那些配角,他们几乎不存在。

由陈忠实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白鹿原》(2017)剧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成功的样本,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几乎每个人物都有着鲜明的特点,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都有着属于自己难忘的特征。这才是宏大叙事的样本,但是余华并不擅长塑造这样的人物。这种短板在他早期的先锋性很强的中短篇中并不明显,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就是用叙事推进,不需要人物为自己代言。但是在长篇小说中这个缺点就凸显出来,《文城》里大多数人物都没有意义,很多细节也没有意义,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不够鲜明,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叙事空间去留给他们,让他们变得圆满起来。
这就导致了《文城》这本小说叙事上最大的弱点,因为采取了传奇故事的框架,加上动乱时代的背景,好像往这个框架里塞进一些人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小说人物的动机不清楚,心理不明朗,行为也会觉得不可信,自然每个人物都是扁平的,我们没有感觉到人性的复杂之处。这就是余华的一大败笔。
在《文城》里,除了土匪和军阀这些明显的坏人角色之外,林祥福的一生没有遭遇到一个坏人,他南下寻妻,把全部家产留给仆人田氏兄弟。田氏兄弟多年后得知林祥福在溪镇安家,毅然把所有家产归还。林祥福死后,田氏兄弟接他的灵柩北上归乡。田氏兄弟可谓义仆。林祥福在溪镇遇到的每一个人,陈永良夫妇,大乡绅顾益民,妓女翠萍,包括小美和阿强,以及他们公婆,所有人物都是良善之辈。他们身边没有一个恶人,恶人都是从外面入侵的。这些卑微的小人物,他们谨遵乱世生存基本人性和规则,谨遵溪镇传统的伦理道德,不敢越雷池一步,无论这种道德伦理是否合理。

由余华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活着》(1994)剧照。
余华津津乐道,用了很多残酷的细节描述土匪如何虐待百姓——这些描述酷刑和虐待的细节,让我们在恍惚之间看到了余华早年写作的影子,可惜,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手持手术刀一样的作家余华了——同样用了无数的细节来刻画乌托邦里的普通人,如何遵守传统伦理给他们划下的界限。某种程度上,小美和丈夫阿强,小美与林祥福,他们自身这种混乱的爱情也是这种扭曲的伦理关系的产物。但是余华用乱世法则规避了这种乱世伦理中的不合理性,把它打造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田园童话。
为什么这些人物都让人觉得不可信?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好人,而是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是鲜活的,他们只是余华笔下的提线木偶,不是因为行动和话语才塑造出来的合理性。《文城》里最鲜活的人物大概只有寥寥几个,而且都是很次要的人物,比如土匪“和尚”,被土匪割掉耳朵、懵懂意识到爱情的陈耀武和他的母亲李美莲等。出场的人物很多,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人物都是轮流上,能让人记住的太少了,很多人物的存在根本就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满足作家宣泄的快感。
以小说中大土匪张一斧为例,书中总是不停地标榜他的恶名,说他杀人不眨眼,三年抢劫了五十七次货船,砍死了八十九名船员,还爱吃黄酒爆炒出来的人肝,还说他七年娶了七个妻子,七年又杀了七个妻子等,这些细节铺陈了不少,但是我们还无法贴近这个人物,总觉得他的眉眼还是模糊的,性格也是模糊的,立不住。
这样的描述,还不如那个看上了林百家的副官李元成,出场只有很短的篇幅,但是得知了林百家已经许配给了顾益民长子顾同年之后,小说中写到,年少英俊的副官站住脚,对林百家说了一句:“记住我,李元成,将来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大英雄李元成,必定是我,你若是落难了,就拿着报纸来找我。”很简单的一句话,少年的傲气、英气,包括几分的赌气,就把一个求爱不成的少年心性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可惜,这样的闲笔,都用在了无用的人物身上,反而那些重要的人物角色,始终都让人隔了一层。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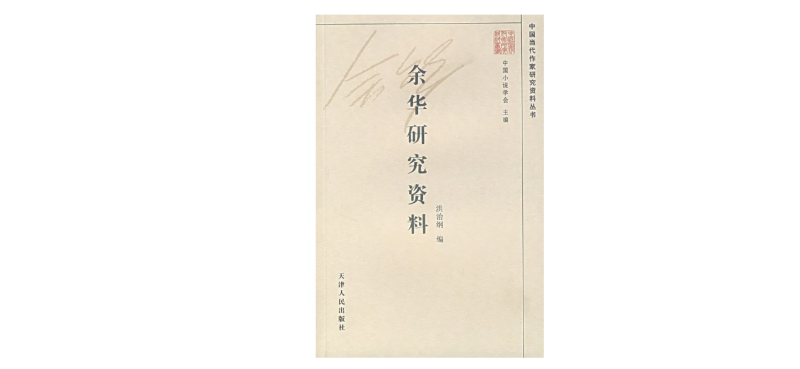
延伸阅读:《余华研究资料》,洪治纲 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评论者是没有资格要求作家如何写,写什么的。比如很多读者会觉得很奇怪,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余华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包含着陈旧的道德观念的民国的传奇?作家选择了某一种题材,往往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不可遏制的隐秘需求。但是能否驾驭这种题材,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提到作家的一个后期风格问题,成熟的作家越是到后期写作,越是乐意选择一种简约的风格,舍弃原来繁复诗学。这是因为作家的巅峰的创作时期已经过去,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阅历和好奇心去吸收更加新鲜的事物,建构更加庞大的叙事体系,构思更加丰富的人物角色等。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点评《文城》的话,我会认为余华的写作是知难而上,他的平庸性证明了他能力的不足,也证明了他渴望重新找回那个锐气的自己。毕竟,一个成功的作家想超越自己的时候才是更难的。
作者|思郁
编辑|张进 西西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