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联社和《亚洲经济》等多家外媒报道,6月1日,韩国法院对“N号房”主犯赵主彬(自称“赵博士”)进行二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42年,较一审减刑3年。“N号房”从被报道起就是韩国最受关注的社会新闻,整个事件震惊世界,包括在中国也多次引起激烈讨论,并上热搜。

“N号房”主犯二审被判有期徒刑42年。来自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画面。
自2018年起,赵主彬等多名犯罪者,以模特兼职等事由为诱饵吸引年轻女性,哄骗她们上传不雅照及视频,并威胁拍摄性剥削视频。其中,赵主彬涉嫌胁迫数十名女性进行拍摄,还指使共犯性侵未成年人。他们将视频上传至即时通讯软件,供付费会员观看、下载。
而即便只计算付费会员,在韩国,也有二十余万人参与观看。网友感叹,“韩国总人口才5000多万人,基本等同于韩国女性每遇到100个男性,其中就有一个可能是会员”。若是算上其他渠道的观看者,数目或更令人震惊。因此,“N号房”也被认为是一种巨大规模的“集体性侵”。在这里,每个观看者尤其是付费会员都是共谋者。自事件被曝光并被议论之后,在韩国,人们数次发起讨伐,要求公布会员信息。在中国也有“国内版N号房”,尽管具体犯罪做法有所不同,在主犯被审判后,也可看到同样的诉求。然而,在现代法律的范畴之下,从个人隐私到具体的事实界定,这一种诉求都极其复杂,不可能实现。

韩国电影《素媛》(소원 2013)画面。
公布会员信息,哪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举措,实际上都已经是一种惩罚机制。也可以说,这正是人类社会使用时间最长的惩罚方法之一。在法律尤其是刑法限制不了的地方,人们通过形成公共意见,“污名”“羞辱”某个犯错的人,以达到惩罚的目的。就像法学家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在《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中提到的,这是一种强大的、有着漫长历史的力量。
现在,无论是韩国“N号房”,还是被查封的国内版“N号房”,多名主犯都已被审判。如果我们认为,参与观看的是共谋者,且同样对事件负有责任,“法律管不了”,那么是否需要实名接受道德评判,也就是这里说的“羞辱”?
当法律审慎地前进时,在某些时候可能无法匡扶正义;“羞辱”机制,是古老的,却显然也是充满高度风险的。弗里德曼在整理法律史的基础上,试图呈现这一惩罚机制的特征和局限。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朴素的正义,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失控,甚至摧毁人性。我们整理他在新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去思考现代法律和“羞辱”机制各自的力量、局限。或者说,可能比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中至少还需要形成一种真正的羞耻文化,否则没有人认为那种行为是可耻的,认为那只是“是个男性都会犯的错”,“羞辱”根本无从谈起。
原文作者丨[美]劳伦斯·弗里德曼
摘编|罗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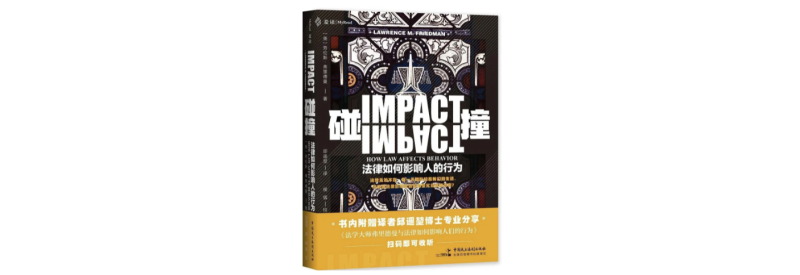
《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美]劳伦斯·弗里德曼 著,邱遥堃 译,麦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3月。
01
污名指的是识别或标记违反某种规范或规则者的外部标记或标签。羞辱指的是愧疚与难堪的感情,它是污名或某种其他形式的标签,可以在被污辱者心中激起的情绪。污名是强有力的惩罚,而羞辱对行为有强大的作用。但污名和羞辱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相同。一个人感到耻辱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是荣誉勋章。对某些人而言,逮捕、传讯、坐牢都不是羞辱,但对一个因商店行窃而被捕的中产阶级而言就并非如此了。
污名和羞辱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效果明显。过去,美国殖民地,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清教殖民地持续且夸张地使用污名和羞辱。每个人都知道著名的猩红字母——通奸的标记,也是纳撒尼尔·霍桑的著名小说的书名。

纳撒尼尔·霍桑小说《红字》中译本(胡允桓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12年11月)封面。
猩红字母不是虚构出来的,1701年新罕布什尔州的一部制定法规定在通奸者的“上衣”上缝上“两英寸长且大小合适的大写字母A”。今天参观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游客们觉得那里的枷锁很有意思,他们把头探进枷锁里让朋友给自己拍照。但这在17世纪可不是开玩笑的,它会在整个社区面前让人蒙羞。1638年,在弗吉尼亚偷“一条马裤”的仆人必须在星期天脚锁足枷坐着,并把马裤挂在他脖子上。1671年在缅因州,一个名叫莎拉·摩根的女人因打了她的丈夫,被强迫“嘴里塞着东西在镇民大会上站半个小时……并把她犯罪的原因写在她的额头上”。相比于锁几个钟头的足枷,猩红字母是更为持久的行为不端标志。对入室盗窃而言,根据《马萨诸塞殖民地自由权法典》(1648),惩罚可以包括割掉一只耳朵。这不仅是痛苦,也是耻辱,它会伴随违法者的一生。
在这些殖民地里,惩罚总是一项公共事务。鞭刑是最常见的惩罚之一,一般在城镇广场实施。鞭刑在生理上是痛苦的,但也是羞辱性的。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领袖和牧师会有意使用污名和羞辱,他们相信这是强力且有效的威慑手段。当时的社区很小,相对同质化,至少在宗教上是同质化的,而且人们很难逃脱公共意见的巨大力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里很可能存在大量有关规范、道德价值、宗教理想的共识。只有这种共识才能使羞辱刑发挥作用。公开惩罚也有教化作用,它就像某种教化剧,向社区传授道德课程。绞刑也在公共广场实施,被定罪的人有时甚至会在绞刑架的阴影中发表演说,谈论使他陷入悲惨境地的罪恶和错误,警告听众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后来,到19世纪,羞辱刑不再流行。在多样化的大城市里,你不再能认为它们发挥着教化剧的功能。人们不再被关在小社区里,很容易离开城镇,逃离当地压力或单纯融入城市人口。特别是,公开绞刑似乎不再有益处,不再是道德教化的载体。现在在拥挤的城市里,它们似乎反而会引起暴民的血腥欲望,于是被废除了。
在内向型的小社区,或者像日本这样有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行事的社会(至少在某些研究日本社会的人看来是如此)中,污名和羞辱仍然有最佳的效果。理论上,污名和羞辱在现代复杂社会中效果不会很好,这里很少有关于规范的共识,很容易逃避同侪群体意见的沉重负担。当然,羞辱并不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羞辱可以因为朋友、家人或同事的看法而对一个人造成痛苦和伤害。

02
一些学者认为污名和羞辱具有更大的作用,甚至在我们的社会、在异质性的大城市亦然。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生活在异质的大社区而非天然的小乡村,污名和羞辱仍在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

《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修订版),[美]詹姆士·Q.惠特曼 著, 佀化强、李伟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
法学家詹姆士·Q.惠特曼(James Q. Whitman)曾竭力主张:甚至“在一个现代、匿名的城市社会里”,羞辱制裁仍有潜力。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一项较早的研究将入狱记录的污名与医疗事故诉讼对医生职业的影响进行对比,发现诉讼的影响要小得多。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医疗事故诉讼当然会损害一个医生的声誉和执业。公开嫖客们的名单,会使其中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男性感到难堪;对一个福音牧师而言,就可能是毁灭性打击。说一家企业的坏话肯定会损害其业绩。如果一家餐馆的窗户上挂了个巨大的牌子,写着这家餐馆有老鼠、蟑螂,卫生很差,还会有多少顾客光顾呢?如果这个牌子写着“这家餐馆的老板打老婆”会怎样?惠特曼不是很担心污名和羞辱对“受害者”的影响,“受害者”甚至可能不在乎。成问题的其实是:羞辱措施获得了公众、受众的支持。污名是有效的,因为它激起了共同体的回应。因此,它是一种形式更温和的私刑,煽动并召唤民众,而且可能很容易失去控制。它适合于“搅动恶魔的政治”,适合于压迫;它“邀请民众去翻查人心中最丑恶的一些角落”。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画面。
因此,羞辱和污名仍是强大的武器。它们在今天特别有力,在这个大众媒体、社交网络、Youtube和其他自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谣言、八卦和批评能够以光速传播。对轻微违法行为的惩罚相比于“犯罪”而言,可能极不相称。不幸的韩国“狗屎”女孩就是一例。她的小狗在地铁车厢里排便后,这个不走运的姑娘拒绝进行清理。她的行为当然不值得称赞,但也够不上死罪。不幸的是,博客和视频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她的“罪行”,使她成为数百万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受到羞辱后失去了工作、朋友和自尊。这也是“报复性色情”的时代:把前女友或男友的裸照或暴露性照片放在网上,供数百万人观赏。
每个社会都有自认为羞耻的事件、词语和情境。在某些社会中,人们避免走上法庭,因为整个群体会对此不满。破产可能是可耻的,至少有点可耻,甚至在现代发达社会亦然。离婚曾是相当可耻的,但在今天这种羞耻感少了很多。羞耻感当然会影响破产率或离婚率。在同居和性革命的年代,婚前性行为在大部分社会和发达国家中不再是一桩丑闻。在美国,1970到2000年之间,同居但不费力去结婚的伴侣数量增长了十倍,达550万人;到现在,这是“适婚人群大都经历过的事情”。欧洲的情况也越来越是如此,特别在北欧国家(如瑞典)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这些伴侣生出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但非婚生子女的污名在社会和法律上已几乎完全消失了。
03
总的来说,人们热烈争论羞辱措施的作用:它们是否应该有效、是否可能有效。问题是:羞辱不是一个简单现象。羞辱可以是贬低对方,让他出丑;也可以是残忍手段,极为反人性。许多现代社会使用羞辱作为一种贬低,作为惩罚,也作为威慑(既有一般威慑也有特别威慑)。但总体而言,清教徒使用羞辱的意图有所不同。对清教徒而言,羞辱可能是重返社会的过程中的一步。猩红字母、烙印、割掉耳朵,这些是持久或永久的。但脚锁足枷坐着或在教堂挂牌一天,这些是短暂的。它们的目的是给违法者和共同体一个教训,最后,违法者应当重返社会;于是羞辱就成为使罪犯重返社会的手段。也就是说,宽恕伴随着羞辱,羞辱是一个教训。羞辱是从罪恶或犯罪回到共同体庇护所路上的一步。
耻辱是一个复杂概念,也是一种具有许多侧面和种类的情感。此外,正如惠特曼所提醒的那样,耻辱借助了受众的力量,而这可能有点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会有危险和局限。甚至布雷斯韦特这个重整性羞辱的专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讲过一个澳大利亚战俘的故事,这个战俘被他的同伴指控偷钱,然后被战俘集中营的“袋鼠法院”审判、定罪、羞辱并“判罚流放考文垂”(也就是受同伴排斥)。结果,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几个月后就死了。就在那时,他的同伴发现他完全是无辜的,是老鼠偷了钱并用来做窝。羞辱是强有力但危险的。布雷斯韦特承认,它可以被用于“减少多样性……或单纯压制多样性”,可以成为“多数人暴政的首要武器”。
但布雷斯韦特还是坚持认为,现代社会可以在对抗犯罪与违法的斗争中更多利用重整性羞辱。现代社会——当然包括他自己生活的社会澳大利亚——很难说是小型的面对面社会,完全不像17世纪的清教殖民地,甚至不像现代日本。然而,每个人还是某些小型网络或团体的一部分。当羞辱在家庭、团体或网络内部运行时,它是重整性的,其实施带有尊重甚至爱意,保留了宽恕和回归团体或社区的机会。它大概是用来改造囚犯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

04
复杂社会是多元化的。许多机构负责制定并执行规制,其中只有一些规则是“法律”规则,也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学者们所谓“法律中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就是个神话——这一观念假定正式制度,也就是在名义上掌权的制度也在实际上统治社会。另一个神话是“神奇的法条主义”,也就是这样一个观念:规则会自动转化为行为。事实上,在社会中,不同规则体系和规则执行相互竞争(与合作),存在许多(正式)法律制度的替代物。

活的法律是一锅热腾腾、乱哄哄的伦理和社会规范大杂烩。人们的行为遵守一套复杂的规则,但不必然是法学院教授的那些法律。
有关小型亲密团体中同侪力量的一个突出实例,来自对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大西洋上一个孤独荒凉的小岛)的一项较早的研究。只有几百人住在这个岛上,以种土豆和捕鱼为生。一群学者在1930年代到访了这个小岛,早在电视、卫星、互联网和其他形式的现代通信方式产生之前。这座岛几乎完全疏离、隔绝于外部世界。(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访问者主要对鸟类生活这些事情感兴趣,但团队里还有社会科学学者,他们研究了岛上共同体的生活,但没有发现任何我们可以按惯例称为法律制度的痕迹:没有警察、律师、监狱、法官、法院。但他们也同样没有发现在其他地方会被认为是严重犯罪的行为痕迹,例如谋杀或强奸。这里不存在正式“法律”,(似乎)根本不需要。
是什么使这个地方成为这样一个良好行为的典范?是同侪群体,是我们可能称为公共意见的压力。岛民们完全被困在这个岛上,可能一年才会来一艘船。他们相互依赖以谋求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这里的每个人都了解每个其他人,他们的生活完全透明,受“共同体敏锐的警觉”所支配。在这些条件下,非正式规范、同侪压力就强大到无法违背了。
如果同侪希望我们服从法律,我们就会服从。如果同侪说不要服从,这也可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同侪:他们可能是父母、亲戚、密友、团体、帮派、部落、职业团体,或者就是普通人。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什么一般结论吗?小型的面对面社区或多或少是自治的,同侪力量足以使成员遵纪守法。但并非所有这些社区都是温和且治理良好的。居民少于100人的皮特克恩岛,就像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一样遥远、与世隔绝。但它可以说完全就是后者的反面。皮特克恩岛上到处是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在某种意义上,这座岛的隔离状态使之成为一种监狱,而“囚犯”就会采取与之相应的行为。监狱本身也可能是面对面的社区,囚犯只能接触到彼此。监狱生活就像岛上生活一样,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船从来都不会停靠这里而已。监狱长和狱警在名义上掌管这里:他们设立了基本规则,也可能在暴动和反抗浪潮期间严厉镇压囚犯,但在许多监狱里,囚犯享有大量的墙内自由。结果是最残暴无情的囚犯们经常结成黑帮进行统治。
同侪压力是一件强大的武器,但大量实验显示,它可以被操纵。像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这样的封闭社区里压倒性的他人力量,同侪压力都在发挥作用。它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力量。它可以促进对国家规范的遵守,也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推进。但显然,同侪压力,或者说公共意见的压力,是影响威慑的关键因素。
本文内容经麦读授权节选自《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一书,内容有增删,部分文字顺序有调整。
原文作者|劳伦斯·弗里德曼
摘编|罗东
编辑|西西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