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构思过程
一个19世纪作家的作品得到20世纪理论家们的关注,这并不罕见,毕竟所有的伟大艺术都有前瞻性。然而这部小说能够得到充分讨论,却几乎不是以一种艺术的方法,而是用一种全然哲学化的方式,仿佛它不再是一个独立自洽的艺术作品,而成了某种哲学观念的形象化注解。
《布瓦尔与佩居榭》的构思成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甚至比福楼拜其他小说都更复杂曲折。根据李健吾所著《福楼拜评传》第七章所转的相关记载,小说可能最早构思于1843年左右,作家的挚友杜刚在《回忆录》中提道:“从1943年起,他就同我讲,他有意写两个誊写员的故事。这两个誊写员,偶尔继承了一笔小小的财产,立刻辞去职务,归隐田园……”这即是《布瓦尔与佩居榭》最早的情节构思。

《未竟的杰作》,作者: (英)伯纳德 ·理查兹 主编,译者:沙丁,版本:双又文化|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5月
而到了1850年,从一封写给另一友人布耶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小说的进一步构想:“你想到《入世语录》,好极了。这本书全然写成,前面来上一篇好序,说明为什么写这部书,目的在使大家返回旧制,返回秩序,返回一般的规仪,同时用一种特别的样式排出来,读者看到,还不晓得人家在取笑。是也罢,不是也罢,这或许是一部可以成功的奇书,因为这非常应时。”
这里的《入世语录》和两个誊写员的故事有什么关系?从后面构思成型的作品来推测,这个“语录”很可能就是小说第二部分《庸见词典》的最初构想。而对应于这一部分的那个“好序”,则由誊写员的故事接上,继而使整部作品呈现出相当奇特的结构。果然两年后,在给情人高莱女士的一封信中,福楼拜又写道:“我有时心中骚痒难耐,真希望谩骂整个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十年后,在某个大框架的小说中,我会做到的。目前,一个老想法又冒了出来,就是我的《庸见词典》。(你知道这是怎样一部书?)序言尤其让我激动,它本身就是一本书,凭我构思它的方式,哪怕我在里面攻击一切,也没有法律能抓到我的把柄。它将史无前例地颂扬人们所赞同的一切。我将展示,多数永远有理,少数永远有错。我将牺牲伟人,成全所有笨蛋,牺牲殉道者,成全所有刽子手,而这一切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火箭喷发一般的文体。”虽然直到1872年,在完成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的文本修改之后,作家才开始真正着手为这部小说的创作做各样的准备,但大体的构思,写作的目的,以及作品的整体风格却在20年前就大致定下了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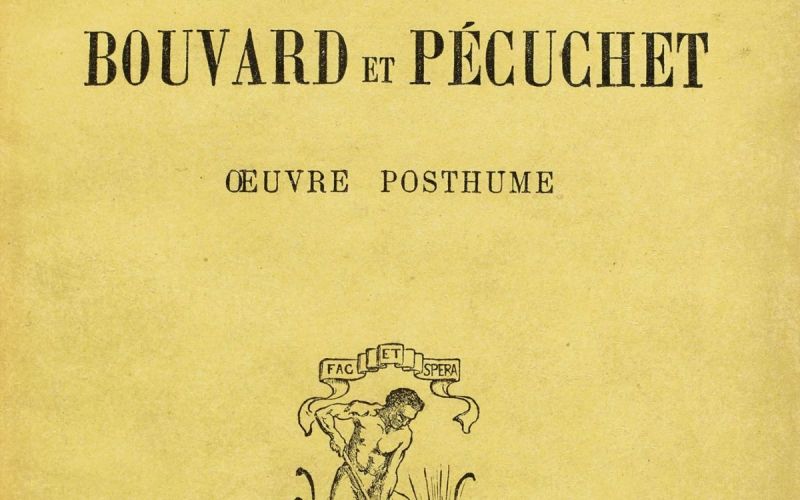
《布瓦尔和佩居榭》书封
正式动笔
1874年8月,福楼拜正式动笔,初步将小说分为三卷。前十章为第一卷,讲述的就是布瓦尔和佩居榭的故事,与杜刚在《回忆录》里记录的差不多:因为一笔可观的遗产而退隐乡下的两位誊写员自学了各种知识,想要尝试一些理想的事业。然而,他们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干脆重新干起了抄写的营生。小说第二卷则完全由引文构成,内容就是这两位主人公在第一卷中所读书籍的各种摘录。第三卷是结尾,作家计划稍加交代二人之后的故事便完成小说。福楼拜原本预计两到三年内就完成这部作品,然而事实上,小说的推进相当困难,直到去世,他也只完成了整个第二卷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布瓦尔和佩居榭》是一部结构新颖的小说,也很符合它的作者对形式的一贯追求。在一部叙事作品中嵌入大量的非叙事性文本,使小说游走在虚构与现实,事件与观念之间,加上这种前卫的类似于“三明治”的结构,也难怪问世当时会被一些保守的批评家诟病。直到近一个世纪以后,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才发现了这部作品中耀眼的现代性元素,并将之视为有关现代世界的一则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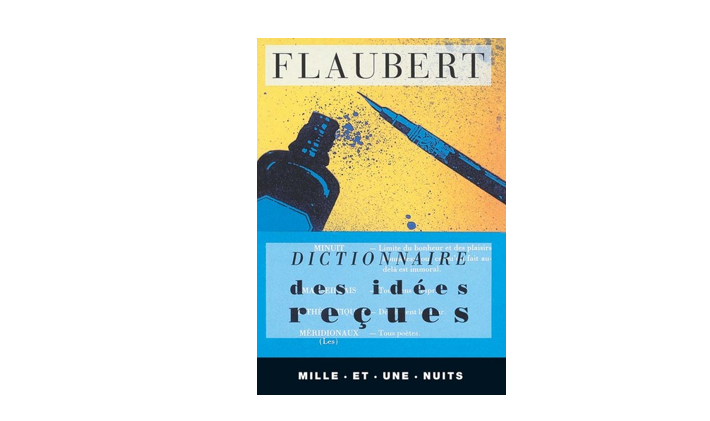
《庸见词典》初版书封
但与其说巴特看重的是《布瓦尔和佩居榭》这一整部小说,倒不如说其中的第二章,也就是《庸见词典》更能引发他的阐释热望。与19世纪的批评家们不同,巴特不再试图去判断这部小说本身是否能构成一个合格的“叙事作品”,他关注的是语言,确切地说,是福楼拜对语言的态度。同样,他也看到了作者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厌倦,这厌倦表面上看是针对精英化知识的,于是产生“庸见”一说;然而事实上,这更是对用语言来建构知识大厦这样一种行为的厌倦。福楼拜,或者说巴特,他们不但厌烦“庸见”,更嫌恶“词典”。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将客观世界抽象化为一种语言,继而进行分类和结集的方式,确实足以成为他们嘲讽及讪笑的对象。
在作家所生活的19世纪,各种门类的“百科全书”可谓风靡一时,从记录专业或日常对话或术语的杂本语录,到指导上流社会女士如何更有效社交的小册子,这种类似于袖珍辞书的综合性体裁也吸引着福楼拜。其实,“百科全书”,或者说编撰“百科全书”的思维方式并非新兴事物,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就以他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博物志》闻名于世。这部充满了奇幻想象的自然科学研究著作,在当代人看来不但与人类早期文明中的神话思维颇为相似,更是充满了瑰丽的文学色彩。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那些倾向于靠人的知识、智慧和广博见闻来征服客观世界的时代,都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百科全书”,但到了福楼拜时代的法国,这种渴望把握知识的“雄心”却渐渐变成了某一个特定阶层拿来玩味摆弄的雕虫小技,鲜活的事物或者现象让位于陈腐的描述性语言,人们仿佛热衷于概括,生产各样的警句妙语,而真正的表达和真正的知识却正在变得越来越贫瘠。
未竟之作,《庸见词典》
如今翻开《庸见词典》,你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很简单的辞条,语言简练,大部分内容一旦脱开特定的历史语境,就变得非常莫名其妙。比如冰块:“食用有危险”;荆棘丛:“总是阴森,不容进入的”,等等。时过境迁,回头再来看这些词语的注释,仍然能感受到福楼拜在陈述和记录它们时的某种烦躁,一种由于话语的过度使用,过度阐释而产生的生理上的疲惫。千百年来,人类竟能不厌其烦地将语言的巴别塔建造得如此雄伟富丽,但这非但不能证明人类在语言的创造能力上,会比其他地方的创造力更胜一筹,反而更体现了人的琐碎和啰嗦,及其背后的平庸无能。而这无能和繁琐,却又是通过那看上去相当恢宏,相当庞大的语言表达体系所表现出来的,甚至,这一体系被建构得越是精致、奇特,表达行为本身很可能越是无法到达它所想要的那个具体涵义。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的悖谬带来了巨大的反讽效果,并且是充满了现代性的。而这就是巴特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核心症结:形式的极端精妙与意义的极大丧失竟可以并行不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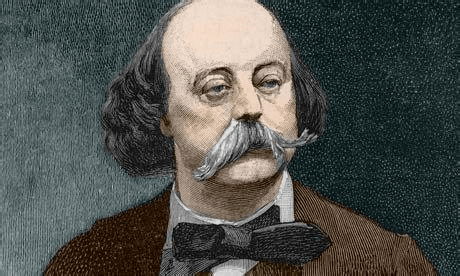
福楼拜
其实,单从《庸见词典》的内容来看,对于那些丑陋而自以为是的公众形象及社会秩序的揭露,作为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历来就不算什么新鲜事。甚至很多时候,对流行文化和媚俗生活方式的讪笑本身也成了媚俗的一部分。比如多年前,一个叫保罗·福塞尔的美国作家在两年之内接连出版了两本著作:《格调》和《恶俗》。它们的内容相辅相成,旨在揭示当代美国公共文化的流弊和虚伪。
但是,它却成为一本畅销的公共读物,因为民众都爱把这类书当成“避雷针”,以掩盖自身对文化已丧失判断能力的事实。要知道文化批判这样的严肃“事业”在当下正和其他许多的“事业”一样,早已被民众的消费冲动和欲望的自我满足所消解,大家需要的是一本简单务实指南,方便带着它穿梭在大街小巷,并按着它的指示悉心分辨出什么是有品位的,什么是庸俗不堪的。正因如此,当福楼拜写作《布瓦尔和佩居榭》的同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波及面”或许太大了,大到连自己也无法全身而退。“我变成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福楼拜语)。于是,当《庸见词典》的批判意图脱离了历史的某个特定的发展时期,连作者自己都会深感他揭示的其实是人类借着话语所展现出来的存在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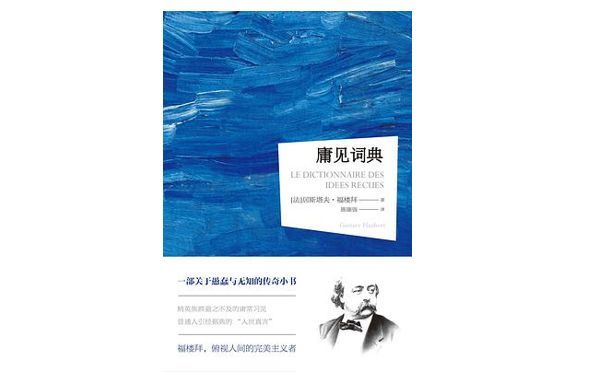
《庸见词典》,作者:福楼拜,译者:施康强,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我变成了他们”,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小说会成为一部迟迟不能完成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作家对自身创作意图的恳切反思:即当布瓦尔和佩居榭所记录下来的一切“庸见”以及它们所指向的“庸众”,被预设为是可以触及人类生存本质上的主体意识匮乏时,也就意味着这一不容辩驳的“事实”本身可能是缺乏艺术表现力的。当任何人在一天中都不可避免地说到这词典中收录的某些话语时,所谓的“个性”还能成为一个标准吗?福楼拜通过对缺乏个性的极端反讽确认了唯有平庸才是无限的、绝对的,人的趋同性于是成为作家创作生涯中最不愿面对也最难以逃避的一个普遍现实。并且,这一现实最终征服了他的写作,将他创造性的艺术语言笼罩在庸俗本身的乏善可陈之中。这可能就是写作带来的反噬,当我们凝视一个重要的问题时,我们认为自己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完整地把握它,而事实上,我们最终可能是在被它把握。福楼拜的方法就是他的艺术反讽,但他对所要批判的那个对象自始至终都抱有一种不彻底的心态,那么这个独特的,被使用得炉火纯青的方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作用呢?
《庸见词典》的译者施康强先生在后记中写道;“他(指福楼拜)让人们相信只要简简单单接受一种内心纪律,就能剥离自己身上那个资产者;只要他们在私底下练习高尚的思想,便能继续问心无愧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和特权。”作家一生蔑视那种布尔乔亚式的矫揉造作,他相信他的写作就是在试图重新构建一种“内心纪律”,并相信这就是艺术,至少是反讽性、否定性艺术的独特功能。然而,作家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而他所信奉的“艺术的否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否定,又应该如何否定,否定到何种程度呢?可以说小说中的反讽,正是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极致,但也来到了其自身的边界。
作者 | 陈嫣婧
编辑 | 宫子
校对 |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