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黑一雄访谈录》,作者:[美]布莱恩·谢弗、[美]辛西娅·黄 编,译者:胡玥,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原作者|辛西娅·黄
摘编|张进
石黑一雄的前两部小说均取景日本,第三部以英国为背景,第四部选取了欧洲一个不知名的国家,最新的一部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伦敦和上海。评论家们深入探究了这些背景和相对应的历史语境,从而挖掘出它们的象征或隐喻含义,并找出作者的哲学视角。石黑一雄本人更愿意将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对人类经验世界性或共通性的表达,这是在阐释身为作家的愿景或目的时他提到的奋斗目标。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日裔英国小说家。1989年获得“布克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20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读者看小说不应该主要为了弄懂史实”
辛西娅·黄:1989年,你告诉大江健三郎:“我其实并不在意我的虚构世界与历史现实是否吻合。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才是我——一个创作虚构艺术的作家——所应该做的:我应当创造我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对着现实的样子照搬照抄。
你现在如何看待历史现实与小说创作间的关系,比如尤其就小说中的上海和日本而言?
石黑一雄:我的言下之意不是说,历史学家也许早已将某段历史中的事实或者当时的情形盖棺论定,而小说家对此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想要强调的是那些并非小说家的首要关注。我想说,读者看小说不应该主要为了弄懂史实。我是在借用历史;我的意思是,我不希望我滥用了历史,但是没准我也会偶尔为之。
黄:小说家的作品和历史学家的作品相比,主要区别是什么?
石黑:历史学家不得不以严谨的方式处理史料。他们必须摆出事实,必须带着学术的严谨为他们理解的历史而辩护。我没有这样的义务。我可以把历史当成故事的发生地。我觉得通常我都是这么做的。我选取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它有助于引出某些主题。
最后,我希望人们在阅读我的作品时,不是因为可以借此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而是因为我也许可以与他们分享一些关于人生和世界更抽象的构想。
黄:小说家对这样的人生构想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石黑:我的确认为小说家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每隔几年总有某种大屠杀回忆录招来人们的反感,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谎言贻害无穷。呃,最近就有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威尔科米尔斯基事件”,这就是个反例。他的作品1995年出版,摘得多项奖项。人们以为这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大的小孩写下的一部纪实文学——这本书叫《碎片:回忆战时童年》——几乎是一夜之间,它成了——或者说似乎成了——大屠杀写作的里程碑。只不过事实上随后就被揭穿原来是作者捏造了一切。
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并非犹太人,而是个瑞士人。倘若他承认这是部小说,那么一切都安然无恙。实际情况似乎是这样:他想表达的是有关个人生活的某种内心痛苦。他曾经是个孤儿,来自当时瑞士社会的底层;他被一些据他所说对他并不好的人收养。他认为大屠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大——的经历就是对他的人生观的某种恰如其分的表达或者隐喻。
这起事件挑起了有关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之间差异的激烈争论。倘若他从一开始就说清楚自己是瑞士人,也从未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待过,说明白他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创作,因为个人环境与大屠杀毫无关联,他只是觉得自己和大屠杀的幸存者有某种共鸣而已,那么一切就肯定情有可原了。
但是当他言之凿凿地肯定自己当时的确身处奥斯威辛,并且这是一部历史记录的时候,他当然就触碰了底线。这部作品仍然和1995年出版时一模一样,但是如今,它已被弃如敝屣。这本书变得臭名昭著。现在成了全世界的笑话。这是模糊二者(历史和虚构文学)界限的极端例子。
我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你从小说中获取的所谓真相和历史学家意欲呈现的真相相去甚远。
黄:你在小说创作中找到的“真相”是什么?
石黑:我认为它并非像历史学家追求的史实那般明确,事实上也不是在法庭上摆出证据,人们想要弄清来龙去脉时所探寻的真相。这里的真相有点模糊的意味。它就像一个人在说:“这是看待人类情感经历的某种方式。难道不是与你的观点不谋而合吗?”
它诉诸的是其他人对于事实的理解:“难道你不也这么看问题吗?难道你不也这么想吗?”
而且我认为,如果你想表达的内容略有不同或者略为新颖的话,那么你想说的是:“也许你从未这样看待问题,但是既然我这么理解,难道你没有同感吗?”从那层意义上而言,它是对真相的追寻;它并非摆出证据说:“这儿有全部的证据,所以结论必然要变更。”它既不是那种科学真相,甚至连社会科学真相也算不上。在我看来,它更多的就像是在体验人生中找寻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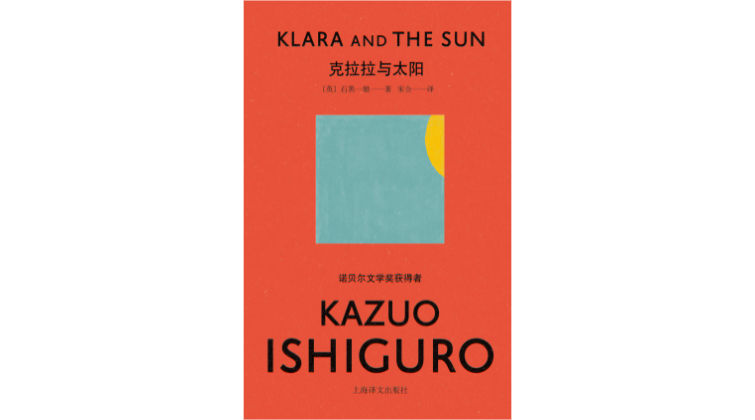
《克拉拉与太阳》,作者:[英]石黑一雄,译者:宋佥,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3月
“当今的写作是一种交流过程”
黄:写小说时,你是否有理想读者在心中?
石黑:没有,对于为什么样的人而写作我其实稀里糊涂。我认为这必然越来越受到实际情况的影响。作品出版后,事实上我要飞遍世界各地,做图书宣传或是接受访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显然我在谈话时对这些人的某种印象不知为何就留在了我写作时的脑海深处。
我的言下之意并不是我会刻意地想到西雅图的某个听众或者在挪威采访过我的某个人。所有这些经历有点堆积起来从而形成了某种读者混合体。这个形象难以辨别清楚,有时候还让人望而生畏,尤其因为我们所谓的全球化趋势。
刚涉足小说创作时,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和我年纪相仿,背景相似,但是随着我去的地方越多,越来越明白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相差甚远的设想,林林总总的当地文化也会随之进入到我的作品中,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存在于头脑中的这个读者。
假如说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是个挪威人,这样一来,很多也许可以书写的东西立刻就化为乌有。我不能用伦敦当地人熟悉而挪威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不能用太多双关,或者仅仅因为措辞睿智,用起来恰到好处,而写上一句让我洋洋自得的话——我不能因为这些缘故而引以为豪,因为等到作品翻译成挪威语的时候,它就会黯然失色。
所以我必须实实在在地扪心自问:“这一句言之有物吗?不是仅仅在卖弄小聪明吧?它的价值在译文中仍然存在吗?”
黄:你如何看待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在你创作其他方面的作用?
石黑:从主题上看,我也许会把某个令当下英国人惶恐不安的大事当成一本小说的绝佳主题,但是再一次,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会在我的头脑中思忖——假如说(这个读者)是挪威人,当然也许是丹佛人或者别的——好吧,对这个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无足重轻。
在我看来,一个人去的地方越多,他就越需要按轻重缓急来回应不同文化下的读者。这位想象出来的读者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辨而复杂。有时候,它会让你束手束脚,寸步难行,对你求全责备。
黄:你讨论了评论界对你作品的反响,认为“克制”“含蓄”“幽静”这些形容你小说内容的字眼让你大为吃惊。知道这些评论是否会阻碍你的某些尝试,或者是否会鼓励并促使你试水其他东西?评论家的言论与你作为作家的举动是否有直接的关联?
石黑:我不知道是否必然有直接联系,但是我无法脱身于评论家的言论。我的意思是,我通常会看许许许多的评论。我从不在意任何个人的评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在国际上出版的好处就在于,浸淫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学文化下的各色评论都尽在你的掌握之中。那么,当人们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我就不能假装这毫不重要。不管我怎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这真实表明了人们对我作品的反应。
不是只有伦敦文学界独有的怪异曲解之风这么理解,而是身在德国或美国中西部或日本的读者通通众口一词。这就能相当有效地断定,在任何时间段内,在广泛的人群范围中,我的创作反响如何。
但是我无法将那样的评论与我或许从书展上遇见的普通读者那获得的反馈割裂开来。这种公众反馈都会左右我,因为我确实认为当今的写作是一种交流过程。部分是因为这个行当要四处奔波,直面读者,我对于这样一个交流过程非常敏感。事情并非仅仅是我碰巧写了这个东西,然后其他人碰巧读到了。事实上,我努力去衡量的是人们如何接受我所做的事,他们理解什么,不理解什么,哪些地方他们觉得过犹不及,哪些让他们忍俊不禁,又有哪些让他们无动于衷。
我认为这些东西十分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了解其他人的方式,了解在作品的反馈上他们与我有多少相似或不同之处。
黄:这样的思维碰撞与你而言有多重要?
石黑:之前我说过——当时你问我小说家追求的真相是什么——我想到的是疑问:“难道你对此没有同感吗?这是我的看法。”我抛给别人的正是那样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回答至关重要。
但是我并不会真的这样回应一众评论,说自己也许更应该这样写,或者那样写;我不会这样去做。
你知道,作品的概述对我来说和评价一样意味深长。他们在概述时,吸引我的是他们会如何总结小说,他们会觉得作品中哪些地方是核心内容,会如何解读某些东西,以及那一切是不是我期望强调的内容。
关于《长日将尽》,之前我会说我很抵触许多人从“日本性”来讨论我的作品,就好像是它们只有对痴迷于日本社会的人来说才有意义一样。我说的是早期作品。我创作的小说以和日本毫无关联的英国为背景——显然,那个决定也许受到了主流观点的影响,因为它们将我的作品看作是对日本社会的历史或者社会观念的阐释。
黄:这些累积下来的反馈促使你审视了作为作家的发展历程?
石黑:《长日将尽》证明,我回应的不是一两位对我应该如何写作指指点点的批评家。恰恰相反,总体而言我是有所不满的,因为人们在我早期的日本小说中过度搜寻信息,就好像我能和人类学家,或者记录日本文化的纪实作家那样,揭示出耐人寻味的信息。
我觉得,可能我想表达的关于人类和人生更共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晦涩模糊。他们没有附和说“哦,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而是说“这些日本人的想法真有意思啊”。
以日本为背景(在早期小说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评价,有点会让读者误解我的写作初衷。所以,那个例子说明作品的整体解读方式会左右我的决定。

《长日将尽》,作者:[英]石黑一雄,译者:冯涛,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5月
“所有人都不得不走出童年保护的肥皂泡”
黄:在你的第五部小说《我辈孤雏》中,读者们不应该心存期待,认为他们会找到不曾在历史书中读到的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某种史实,是吧?
石黑:我认为是这样,他们找不到的。我所做的就是研读能找到的资料。有一两本书是我从珍本书店中淘来的,写于那个年代(三十年代),但是据我所知,书中没有说到不为人知的内容。里面提到了鸦片战争——这点人尽皆知——任何一本关于旧上海的书都会说到那些东西。
人们对上海津津乐道。也许我可以推荐这方面的许多好书,它们由训练有素的作者撰写,这些人追求的是研究艺术的精益求精,通过史料得出结论。
我把上海用作某种隐喻的场景。我是个靠不住的人;要是想了解历史细节,我是不会信任我这样的作家的。(笑)
黄:你能谈一谈《我辈孤雏》中的主旨或者母题的重要意义吗?诸如像“孤儿”,还有《长日将尽》联想到的“伟大”等主旨或主题。
石黑:关于孤儿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孤儿。当然,这部作品里,这些角色的确都是孤儿——他们的父母要么去世,要么失踪。这儿的孤儿状态有隐喻的意味。我希望在此处探讨的是所有人都不得不走出童年保护的肥皂泡,置身其中时我们对外界的凶险一无所知。
随着年纪渐长,我们走入更广阔的天地,懂得了命运多舛。有时候,这一过程温和而舒缓;有时候,对有些人来说,则如晴天霹雳、急风骤雨。主人公克里斯托弗·班克斯生活在相对而言受到庇护的金钟罩里,活在受保护的童年里,他以孩子的眼光看待世界,他认为自己有了天大的麻烦,但其实不过是些小孩子们不要闯祸之类的小问题而已。
突然,他被扔进了成人的世界。问题变成了:当我们走入更险恶的世界,我们是否带着怀旧之情,带着曾几何时我们相信世界是个美好所在的回忆?也许,我们被大人们误导了,也许准确地说,我们被保护着免受这些厄运的侵袭。
之后我们走入了大千世界,发现这里有着污秽之事和棘手难题。有时,也许我们仍然残留着孩提时代的天真想法,并且有着想要重塑世界、拯救世界,想要让世界复原成孩提时代模样的冲动。
所以,最新的这部作品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猝不及防失去了童年天堂乐园的人。随着他的长大,也许是无意之间,他一直持有的人生宏伟目标就是要修复曾经的错误,这样他才可以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
我所说的“孤儿”,指的是最广义上离开了我所说的保护我们的童年世界。

《我辈孤雏》,作者:[英]石黑一雄,译者:林为正,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黄:“怀旧之情”如何植根于克里斯托弗对过去的历史意识?
石黑:最深层意义上的怀旧主题——我说的并不是全球旅游产业有时会兜售的那种怀旧,也不是无害的前工业时代才会有的某种美好而悠闲的过去。我说的是更为纯粹的个人对童年生活的怀旧之情。
有时,我认为那种怀旧可以是支非常正面的力量,也可以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因为就像是理想主义之于才智,那种怀旧之情对情感也有同样的作用。你饱含深情地记起一个时代,那时认为世界是个美好的所在。
当然,有时候这种情绪会将你引向毁灭的举动,但是它也可以让你想将一切变得更好。
黄:帝国主义主题似乎在你的小说中至关重要。人类对历史事件的否认,犯下的罪责或者承担的责任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你的小说中。这部小说呢?
石黑:帝国主义能说的都说完了,我没有什么高见。这本书中对于那些主题都有涉及,但是关于帝国主义没什么惊人发现。
这本书涉及的帝国主义稍有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我们讨论的并不是比如说印度的情形(处在大致相同的时期),英国在那执掌大权,而印度是它的殖民地。我们讨论的是非官方的帝国主义,从根本上说上海仍是中国的城市,外国人只是赢得了所谓的“治外法权”,意思是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限制。
所有这些外国工业家蜂拥而至,并且定下规矩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奇耻大辱。但是那就是当时的军事形势。
所以事实上,这里的背景不一样:敌对势力——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全都虎视眈眈,想要从经济上和工业上占据主导,剥削中国,但是并没有帝国主义概念上殖民别的国家时所谓的那种责任。
即使英国统治者也许有自欺欺人的成分(就印度而言),他们当时的确有要给当地人灌输英式生活方式和英国制度的宏伟想法。这个过程很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剥削。我认为在上海的那些人不觉得自己肩负这样的责任。在很多方面,你可以说他们享受到了殖民的许多益处,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当时并没有任何势力在上海掌权。称其为帝国状态是不严谨的,因为情况并非如此。
黄:你怎么看克里斯托弗透露出的对父母失踪的理解?我们是否应该解读为有关斗争的寓言?
石黑: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小说是仿拟的形式;设定了这些谜团,一定程度上而言,我觉得要想符合这种叙事风格,你得给出答案,所以在那层意义上谜团得以解开。有时候,谜团是在更深层次上得到化解的。我不知道这样的揭露是否意在表达宏大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就是用来推动情节发展的。
也许克里斯托弗的发现——这个原以为是在和邪恶斗争的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从邪恶中获益——有其深意。
这并非恶棍或江洋大盗身上会表露出的某种邪恶——我是说,你无法对邪恶追本溯源。它无处不在,那些初衷良好的人有时到头来就会助纣为虐。那时,他就是个天真无邪的孩童,结果毫不知情地从邪恶中获益。
在小说的开始,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作为一名侦探如何与邪恶斗争:你揭露真凶,把邪恶的精灵放回瓶子里。最后,他发现邪恶天生就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你很难出淤泥而不染或者独善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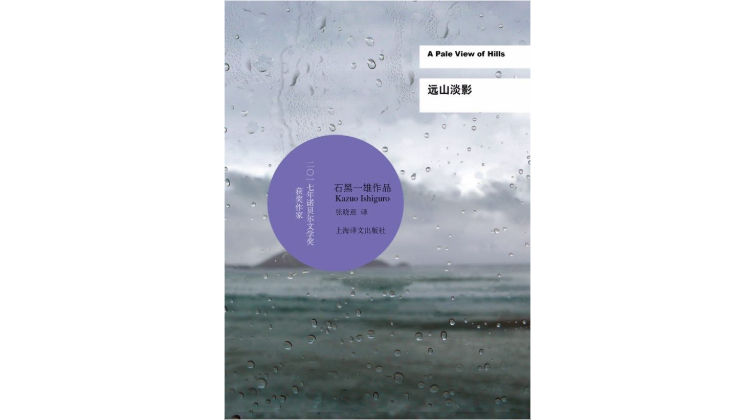
《远山淡影》,作者:[英]石黑一雄,译者:张晓意,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我对于什么角色是男性、什么角色是女性并不十分在意”
黄:有一次我参加会议,会上对你作品的一项批评就是你对女性的呈现很有限。然而,有人指出你的小说处女作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女性口吻来写的。那么这部新作中的女性人物呢?詹妮弗、莎拉还有母亲都在克里斯托弗的探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石黑:呃,我不知道。写小说的时候,我对于什么角色是男性、什么角色是女性并不十分在意。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是意识到的,但是你不一定会在写作时把特点分派给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你创设的人物相互作用,那就是最终呈现出的模样。
对我来说,把《远山淡影》中的佐知子和这本新书中的詹妮弗相提并论有点困难。当然,她们都是女性,但是她们扮演的角色相去甚远,她们截然不同。除了都是女性外,我不知道……
原载于Clio杂志第30卷,第3期(2001年)。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有删节,全文见《石黑一雄访谈录》一书。
原作者|辛西娅·黄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