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购物狂欢节至今已持续14个年头,在抢购热潮之余,“消费主义逆行者”“消费降级启示录”等话题也逐渐引起注意,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陷阱。
11月13日(周日)15:30,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系列活动第142场,我们联合单向空间、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从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近期出版的新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出发,共谈我们的消费经验史。

—— 扫码收看直播回放——
01
“双11”现象与年轻人的消费共同体
刚刚过去的“双11”购物狂欢节,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与去年相比,今年全网各平台的消费数据总和下降幅度达到73%。这或许与疫情以来的经济下行趋势有关,但在田丰看来,集中性消费的放缓未尝不表明新一批消费群体正在回归理性。
“我们以前经历过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期,所以喜欢囤东西,到了‘双11’那天玩儿命清空购物车,过后消费额度会急剧下降。”与之相对,年轻一代对待消费的态度和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对他们来说,那些东西随时随地可以买到,只不过暂时由商家保管,只要有钱,就可以把它们变成自己的。
互联网届有句口号很出名,叫做“得年轻人者得天下”。年轻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代际受到重视,不一定在于他们的生产者属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消费者属性。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在新作《制造消费:消费主义全球史》中,把年轻人视作既有次序的颠覆者,他们通过很多新奇的消费行为,与其他年龄群体的人形成区隔,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作者:[法] 安东尼·加卢佐,译者:马雅,版本: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6月
基于一群人对生活共通的理解、对社会一致的想象,一个虚拟的共同体得以形成。为了融入这个想象当中的共同体,他们需要建立差别,体现与其他群体的差异。
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中,有很多方式可以建立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但在一个节奏很快的社会当中,消费是建立差异最简便和直接的手段。“就像现在,与其跟别人说自己读了好多书,不如直接拎一个别人没有的包、拿一部别人没有的手机更能凸显个性。”
书中还有一个核心概念,讲述消费欲望和道德约束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方面有消费的欲望,另一方面会受到道德观念的约束。因此,田丰认为年轻群体与中老年群体的差异,还反映在他们对道德的习得和认同上,而道德观的差异又会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让他们更容易通过消费这种快捷的方式来建立自我、建立新的共同体。
安东尼·加卢佐以1960年代的年轻人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完全抛弃了父辈节约、远见和禁欲的精神,更加适应现代的工业化、全球化的消费模式。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扩张,1960年代年轻人的消费已经完全打破父辈的消费天花板,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在小市场里买目之所及的物品,而是可以接触更多全球性的消费选择,以至实现精神层面的消费和转变。
新一代人不必局限于小镇、村落,跟同样一批伙伴从小玩到大,而是有机会进入各种各样全球化的社群里。在选择社群的时候,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标新立异,那些距离日常生活越遥远的社群,越能让他们感到有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消费符号、消费标准,需要不断迎合不同社群提出的消费要求。通过不断地满足消费要求,他们可以变成具有社群归属感的个体,被相应的社群所接受,找到心理共鸣和自我意义。
与1960年代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更轻易地打破时空界限,通过海淘购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商品。甚至不必那么麻烦,大家可以直接在拼多多上买一个类似的山寨品牌,够用就可以,还能获得一种和世界潮流紧密相连的归属感,完成全球性和地方性的连接。
田丰提到多年前有位老同学从老家来北京玩,抛给他一个问题,“北京人真的那么有钱吗?为什么在挤地铁那么糟糕的通勤状况下,还人手一部iPhone?”当时在老家,只有买得起私家车的人,才会用iPhone。
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非常一致,所有东西都自产自销。随着都市化发展,存在方式、生活方式逐渐和消费方式脱离。
以前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评价让田丰记忆犹新,“社科院的人远看好像收破烂的。”因为在社科院工作的人大多数时候忙于案头,很少需要抛头露面,几乎没人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现在则不同,年轻的社科院工作人员开始注意形象,虽然工作模式没变,但他们希望通过新的消费方式改变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固有印象。
田丰认为,现在人们的消费不仅仅为了满足需要,而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产品、产出,用消费行为展示整个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02
当我们谈论科技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全书横跨18-20世纪,以1960年代年轻人的消费作结,从历史维度解释西方社会的商品和消费理念如何变更。
开篇有张照片专门介绍法国杀猪仪式,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清晰地展现出工业化和商品化如何让消费者远离生产过程,让消费变得越来越抽象。对农民来讲,从杀猪的第一刀到制作香肠的最后一道工序,整个制作和消费流程非常清晰。但是对消费者来讲,杀猪仪式完全不可见,他们最后只能见到一个完全包装好的抽象的物。
消费的抽象化还表现在它的附加属性上。现在的商品房里,客厅、厨房都是标配,它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更是身份、地位的标志。从前人们住在筒子楼里,只能在卧室里待客、在公共走廊里做饭。随着财富的增长,住房面积不断扩大,有了客厅、厨房,可以把卧室里的隐私、烹饪时的脏乱阻挡起来、隐藏起来。
书中借用鲍德里亚的功能性影像观点,认为住宅是一台“生活机器”,人们在购买用来填充住宅的商品时,表面上购买的是它的功能,实际上是被它看似“有用”的科技和效率因素所左右——这种影响甚至不同于以往一目了然的符号化标识,而是通过潜意识等不易被察觉的方式鼓动人们消费。比如前些年流行的日韩进口电饭锅,看起来是个高科技产品,可以选择米饭的类型,实际上背后隐藏的是你能否买得起这个电饭锅——动辄几千块钱,普通家庭很难负担。表面上是功能层面的消费,其实是地位和阶级的体现。
所谓科技产品,并不一定意味着运用了很多前沿技术,而更意味着让使用者摆脱繁重、琐碎的日常问题,让生活更加舒适、便捷、有效率。就像戴森吸尘器可以用很少的时间把家里的边边角角都吸干净,空气炸锅可以让原本不会烤制的人把食物烤好,评价一个科技产品的好与坏,关键在于看它有没有改变人们原本的生活模式。科技产品改造我们的生活,也改造我们消费的取向。
田丰认为,消费是为了满足两种需要。其一是实用需要,其二是心理需要。基本的生活用品主要是为了满足自我的实用需要,大量的奢侈品则更多为了满足和他者进行比较的心理需要。现在市面上畅销的消费品则二者兼顾,田丰家里买过扫地机、拖地机,“设定好程序,它可以每天按时自动打扫房间”,在满足家庭清洁需求的同时,也不失为一种家庭配套的升级。炒菜机则是一次没那么成功的消费,“它可以把菜炒熟,也可以炒出大概的色泽,但吃到嘴里总觉得不是那个味儿。”
安东尼·加卢佐在书中写道,“二十世纪的母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主妇,她还是一名总工程师,要学会用各种新玩意儿填充住宅,让别人看到一幅便捷的家庭生活景象。”当传统的乡村茅草屋转变为现代化的城市住宅,当个人消费转变为家庭消费,“母亲——全家的消费总管”需要重新规划全家消费的品类、消费的趋势。
她需要为擦桌子和清理衣服而选择完全不同的除尘器具,为洗碗和刷马桶而选择完全不同的清洁剂,为全家老少每一个人而选择完全不同的食物搭配。过于繁重琐碎的工作,让家庭主妇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分配时间、节约时间。
192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家庭合理化运动,以各种科学的组织工作原则,规范家庭事务的操作标准。家用器具因此变得越来越精细,“比如用普通的刀削一斤土豆需要九分钟,但是用剥皮器削同等数量的土豆只需要三分钟,买了这种削皮器,母亲们就可以节省六分钟时间去做更多事情。”
科技产品一方面能够提升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毫无必要的加成。严飞的办公室里配备了一台高端打印机,有移动设备连线功能、远程操控功能等等酷炫的新功能,价格也水涨船高。但对使用者来说,打印机只要具备USB接口,就足以方便地读取、打印文件,其余的功能充其量是附加卖点。严飞以此反思:附加的体验真能提升效率、节省时间吗?使用功能和符号性、宣传性的功能相比,二者哪个更为重要?
03
跳出消费主义陷阱
在近期出版的新书《悬浮》中,严飞描述了他对于消费与公共性之间关系的新体会。他发现菜市场、理发店的功能不仅仅是买卖、消费,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们创造出公共的社群空间。“如果常逛菜市场,可能会发现有些菜贩也许已经陪伴我们很长时间,见证我们人生成长的各种历程。他们也会和你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情,跟整个社区形成很紧密的关联。”从小到大,严飞也喜欢去同一家理发店,在生活中、微信里跟理发店老板形成深度的交流和连接。“我不太喜欢去大商场里的理发店,总觉得少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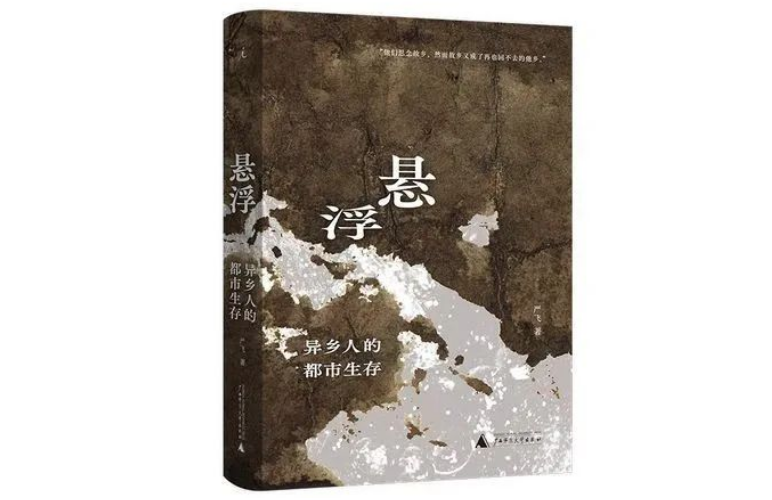
在他看来,消费的场景、消费的体验感远比消费本身重要,它们甚至可以在原本的消费之外,创造出另一层消费。“通过消费,我们不只可以购买一件物品,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平淡之中,收获一种心安。”
近些年,二手商品逐渐在市面上流行。与《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中对历史上丹迪主义、波西米亚风格艺术家的描述类似,现在古着店二手服装价格颇为昂贵,一般可达类似款型新衣的三到四倍。“消费者有意借助衣服的独特彰显自身性格、品味的独特,但如果其他人完全不知道你穿的衣服来自哪个年代、哪个地方,他们怎么会理解你的独特?”田丰认为,售卖这类产品的商店必须依靠文化和环境因素的布局,帮助消费者理解产品的意义,“让别人能够理解我的理解。”
在《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中,安东尼·加卢佐提到消费者对于修辞感、完美感的追逐,导致自己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现代社会的口号是人人平等,但在看似平等的社会中,处于相对优势的社会阶层仍然会极力凸显与众不同之处。“只要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总归会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来。”当传统方式失效,消费就成为展现优势地位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如何真正跳出消费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尝试反抗消费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逻辑,不必过度追求所谓完美的生活、美丽的自我。严飞认为,人有消费的欲望、比较的欲望是正常的,但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里,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变成一种被支配的欲望。就像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书中写道,如果不去消费,人们似乎就会沦为有缺陷的新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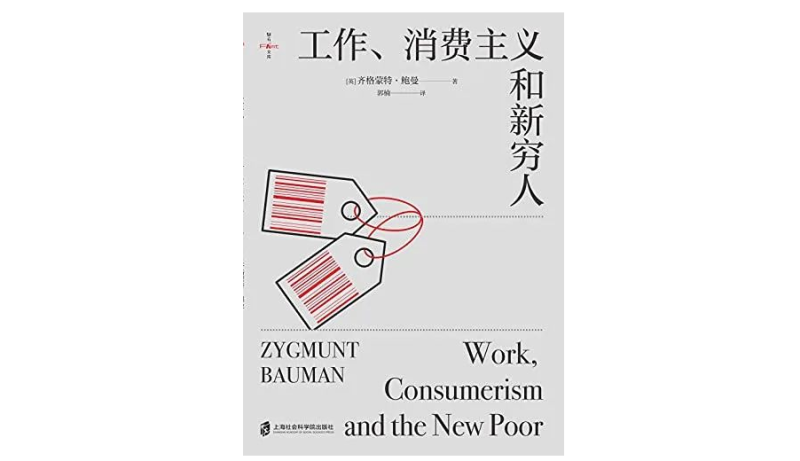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译者:郭楠,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9月
在严飞看来,也许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拥有更多东西,而是拥有更多时间去享受自己购买的东西。“我们家小朋友今年才5岁,每次出门一定要购买一样东西,随便什么东西都行,这样他才会觉得这趟出行物有所值。5岁的小朋友已经有如此明晰的消费取向。”今年暑期,小朋友去北京天文馆参观,在礼品店里买了两只太空对讲机。接下来的整个暑假,父子二人拿着对讲机不断在房间里模拟太空对话,留下非常温馨的暑期回忆。
“这个小小的太空对讲机四五十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却陪伴我们俩度过很长一段时间,陪伴小朋友成长。也许多年以后,小朋友重新翻看他的故纸堆,在旧玩具里找出这个太空对讲机,他还能回想起自己和爸爸在那年暑假的一段经历。”与囤积很多长期用不上的东西相比,囤积回忆或许是更为划算的消费。
消费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无论选择实用的功能,还是符号性的意义,都有其价值和必要所在。在两种选择中找到适度和平衡,或许是避免陷入消费主义陷阱的可行办法。

运营团队
策划执行 新京报书评周刊 万有引力
本文整理 段雅馨
本文编辑 吕婉婷
海报设计 万有引力
本文校对 柳宝庆
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
隶属于新京报的文化领域垂直媒体,自2003年创刊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深耕于文化出版动态,向读者提供有关文学、社科、思想、历史、艺术、电影、教育、新知等多个领域的出版动态与学界动态,提供诸如专题报道、解释性报道、创作者深度访谈等深度文化内容。
2019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基于现有内容资源,推出了“文化客厅”系列活动。文化客厅线下活动,旨在通过与读者的真实交流,建构立体的内容传播方式,与真实的个体共同理解并见证时代的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