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出过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她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倒,之后她完全康复了,但两年后她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和行为怪异的症状。在几个月时间里,她还能继续在诺曼底伊沃托的老年寓所里独立生活,她在那里有一个单室套。83年夏天,在暑热最难耐的日子里,她突感不适,住进了医院。人们发现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她的冰箱里只有一包方糖。从此以后,已经不能让她再一个人住了。
我决定接她来我家,在塞尔吉,坚信在这个她熟悉的环境里,有两个她帮我一起拉扯大的儿子——埃里克和大卫的陪伴,她的症状会很快消失,她可以变回那个活跃独立的女人,恢复她不久前健康的样子。
结果什么作用都没有。她的记忆力继续恶化,医生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她不再认得地方和人,我的孩子,我的前夫,还有我。她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要么在屋里四处走动,要么在走廊的楼梯台阶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84年2月,因为她身体过于虚弱又拒绝进食,医生把她送到蓬图瓦兹医院。她在那里呆了两个月,接着在一家私人养老机构短暂过渡,随后再次住进蓬图瓦兹医院老年部,86年4月她在那里死于栓塞,享年7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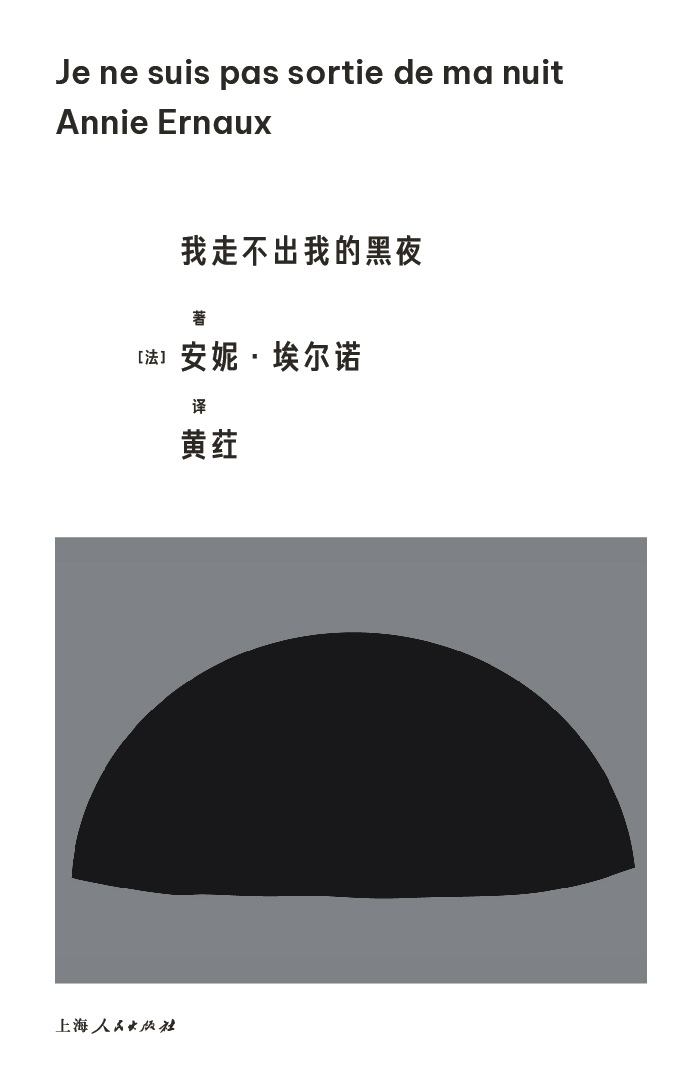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安妮·埃尔诺著,黄荭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1月
当她还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开始在纸片上记录母亲的言行举止,没有写日期,那时的她让我心里充满恐惧。我无法忍受这样的退化会发生在我母亲身上。一天,我做梦梦见自己生气地冲她嚷嚷:“别疯了!”从那以后,当我在蓬图瓦兹医院再次见到她时,我要竭尽全力去写她,她说过的话,她的身体,和我离得越来越近。我写得很快,感觉很强烈,不假思索也没有顺序。
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到处,都有母亲的身影。
85年末,我心怀歉疚,开始写一个关于她一生的叙事作品。我感觉把自己放在她不复存在的时空里。我内心充满了撕裂感,一边是在文字中想象她年轻时迈向人生的样子,另一边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次次探望,把我带到她无法避免的日益衰退的现状。
母亲死后我把这个开了头的作品撕了,重新开始写另一个叙事作品,88年出版,《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我写这本书的整个期间,我都没有重读在母亲生病时我写的那些纸片。它们对我而言仿佛是不能触碰的:我记下了她生命最后的岁月,最后几天,甚至是去世的前一天,只是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她最后的时日。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状态——或许是这一时期我写作的特点——从某个方面来看是很可怕的。这本探望日记以某种方式把我引向我母亲的死亡。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出版它。也许我想留下母亲的一个形象,我们母女关系的一个真相,那是我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试图触及的主题。现在我认为,一部作品的独特性和一致性都应该尽可能地受到挑战,不管你是否情愿使用那些最自相矛盾的素材。把这些纸片公之于众,我认为时机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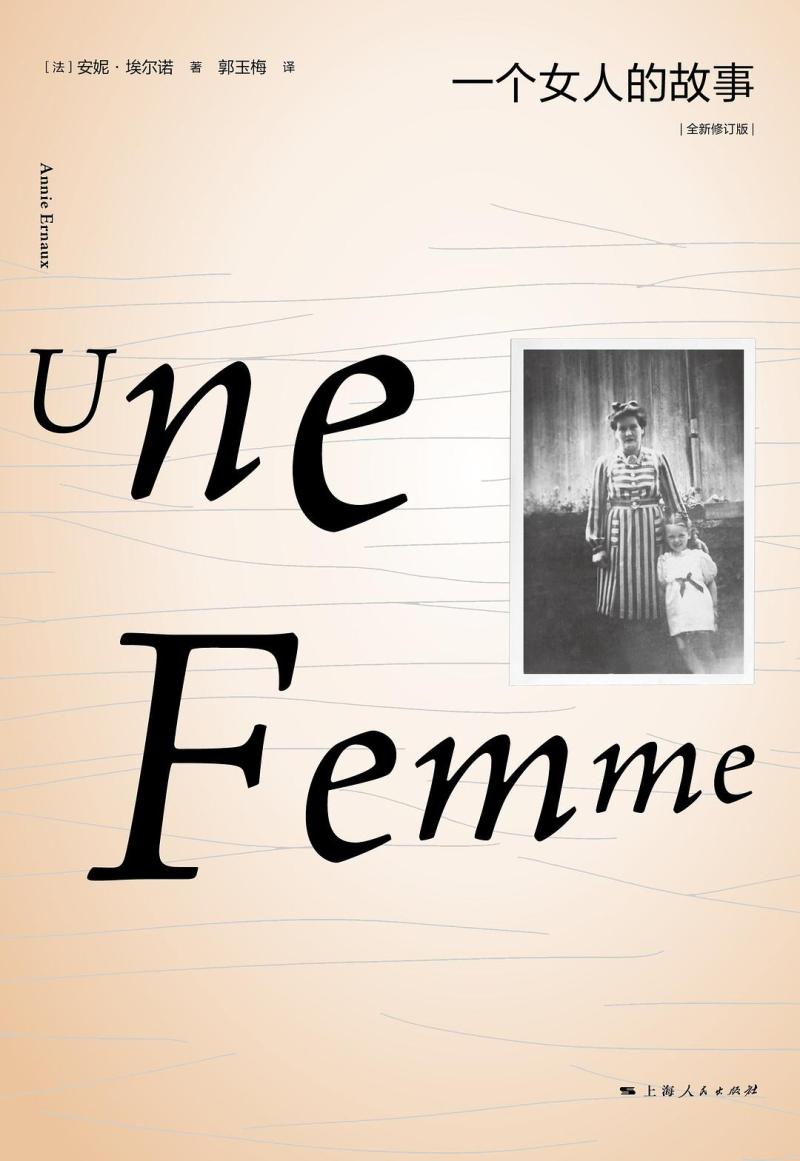
《一个女人的故事》,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郭玉梅,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我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公开,带着我写作当时感受到的震惊和不安。把那些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刻记录下来时我不想做任何修改,仿佛没有了时间概念——或许只有重现的孩提时光——,也没有任何想法,除了一个:“这是我母亲”。她不再是我这辈子认识的那个女人,但在她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容下,通过她的声音,她的手势,她的笑声,她是我母亲,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些文字解读成是对在养老院“长期居住”的客观见证,更不能把它当成是揭露(大多数护工都是细心且敬业的),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痛苦的残留。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经常梦见她,就像在她生病前一样。她还活着,但已经死了。当我一觉醒来,有那么一分钟,我确信她真的以这种双重形式存在,既生又死,就像那些两次越过冥河的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
96年3月
1983年
12月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在起居室。耷拉着脑袋,脸一动不动,松弛。没有张开嘴,但从远处看,就像嘴张着一样。
“我的手不听使唤了”,她说(她的洗漱包,她的开衫,一切)。所有东西她都抓不住了。
她想马上看电视。她等不及我先把餐桌收拾干净。现在她什么事都不理解,除了她自己想要做的。
每天晚上,我们上楼扶她上床睡觉,大卫和我。在镶木地板铺上地毯的地方,她把腿抬得高高的,好像她要下水了。我们笑,她也笑。刚才,当她刚高高兴兴躺到床上,想给自己涂点面霜时,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所有东西,她对我说:“我要睡觉了,谢谢你,女士。”
医生来了。她说不出自己的年龄。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有过两个孩子。“两个女孩,”她说。她把两个胸罩一个穿在另一个上面。我记得那一天,她发现我穿了一件胸罩却没有告诉她。她大喊大叫。我十四岁,那是六月的一个早晨。我穿着连衣裤,正在洗脸。
我又开始胃痛了。我对她,对她的失忆,已经不再生气了。毫不在乎。
我们去商业中心。她想买菈·芭哲瑞最贵的一款包,一个黑色皮包。她反复说:“我想要最好看的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包。”
之后我带她去莎玛丽丹百货公司。这次是一条裙子和一件长袖羊毛开衫。她走得很慢,我要搀着她。她无端端地笑了。女店员们奇怪地看着我们,露出尴尬的神情。我并不尴尬,我傲然睨视她们。
她问菲利普,很焦急:“你是我女儿的什么人?”他哈哈大笑:“她丈夫!”她笑了。
1984年
1月
她总是把她的卧室和我的书房搞混。她打开书房的门,发现弄错了,轻轻地关上,我看到门把手抬起来,就像门后没有人一样。某种不安。一小时后,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了。她再也弄不清楚自己在哪儿。
她把脏内裤藏在枕头里。那天夜里,我想起她沾满血的内裤,她把它们埋在阁楼上一堆脏衣服下面,直到洗衣服的那天。当时我大约七岁,我痴痴地看着它们。现在它们沾满了屎。
今晚,我在改作业。她的声音从隔壁的起居室响起,很平静,就像在剧场演戏一样。她对一个看不见的小女孩说:“很晚了,我的小姑娘,你应该回家了。”她笑了,很开心。我用手捂住耳朵,我感觉自己坠入某种残酷的深渊。我并不在剧院,是我母亲在自言自语。
我找到一封她写了开头的信:“亲爱的波莱特,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现在,她写不了字了。这些字仿佛是另一个女人写的。而这只是一个月前。
2月
在餐桌上,她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她是一个农场女工,我儿子是伙计,我是老板娘。除了小瑞士奶酪和甜食,她什么都不想要。
伊莎贝尔(我侄女)周日在我们家吃午饭,母亲的疯言疯语让她笑得前仰后合。只有我们,她的孩子,我,才可以嘲笑我母亲的疯狂,她不可以。外人不可以。埃里克和大卫说“她太好笑了,外婆!”仿佛,老年痴呆的她,依然那么与众不同。
今天早上她起床,小声说:“我尿床了,我没忍住。”这是我小时候发生这种事时说的话。
星期六,喝咖啡吐了。她躺着,一动不动。她的眼睛变小了,眼眶红红的。我给她换衣服。她的身体又白又软。之后,我哭了。那是因为时间,因为从前。我仿佛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我害怕她死去。我宁可她疯疯癫癫地活着。
3月
15日,星期四
在医院,不,确切地说是在医院养老院的走廊上,二楼,我听见:“安妮!”是她在喊我,人们给她换了房间。她是怎么认出我的身影的,她已经看不见了,或者说完全看不清(她有白内障)。当我走进房间,她说“我得救了”。或许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你在这里”。她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确切的细节:人们强迫她干活,不付她工资,不给她喝水。完全是异想天开。但她现在一直都能认得我,不像她在我家的那段时间。
4月
26日,星期四
可怕的一幕。她以为我来接她,她要离开这里了。她极度失望,什么也吃不下。可怕的自责。不过,有时候,也会心安理得:她是我母亲,但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了。
听祖克[1]说过:“人必须死了,才能确保不用再依赖任何人。”
29日,星期天
我给她刮毛给她剪手指甲。她的手指甲很脏。她很清醒:“我会在这里一直呆到死。”又说:“我尽我所能让你幸福,而你并没有如我所愿。”

《正发生》剧照。
5月
17日,星期四
我去于斯接她。蓬图瓦兹医院老年部接受她长期入住。或许这是她最后一次坐车,她自己并不知道。当我们到了医院院子里时,她的脸色阴沉下来。我知道她以为是回我家。她的房间现在在四楼。一群女人围着我们,她们对我母亲以你相称。“你要和我们一起住?”就像一群小姑娘围着学校里来的一个“新同学”。当我离开的时候,她神情茫然地看着我,惊慌失措:“你要走了吗?”
现在,一切都倒过来了,她成了我的小女儿。而我不能成为她的母亲。
1985年
1月
6日,星期天
新年第一天,我母亲,还有所有老太太都和以前一样,护工给她们穿上了衬衫和裙子。还给她们倒了香槟。生活的假象。想象早晨,护士们从橱柜里拿出衬裙,裙子,把它们套在苍老的身躯上然后喊道:“新年快乐!过节啦!来吧奶奶!”一整天,人们都像真的在过节一样。老太太们似乎在等待。但没有什么可等待的。夜晚来临,护工把她们的衬衫和裙子脱下来。就像小时候,我们玩扮装游戏、假装过节一样。但在这里,是这一切背后,永远不会再有真正的节日。
她说:“人生当自强。”又说:“如果不够强大,就该机灵点儿。”过去我们只想着奋斗。我用未完成过去时来谈论她。然而,现在的她和以前的她是同一个人,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5月
18日,星期六
她今天比以往都消沉,拒绝见我。天气很好,她坐着轮椅,我笨拙地推她到花园里去。我意识到我已经习惯了她的衰老,习惯了她那张和以前不一样、冷漠的面孔。我记得她开始 “离开”的那个可怕时刻。她在屋里不停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她找不到的东西。(后来,我想到了安纳西花园里的乌龟,在秋天绕着栅栏和小路四下奔走)。她还写下:“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1986年
4月
7日,星期一
她死了。我无比痛苦。从昨天早上到现在,我一直哭。我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一切都在那里。心跳停止了,是的。痛苦无法预知。强烈的想要再见到她的欲望。这一刻突如其来,出乎我的想象,出乎我的意料。我宁可她疯疯癫癫地活着也不愿意她死去。
我想吐,头痛。我曾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和她和解,但我做得远远不够。昨天没有想到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我昨天带给她的迎春花还插在桌上的果酱罐里。我还给她带了“森果”巧克力,她吃了一整块。我给她刮了脸,喷了古龙水。结束了。那是“生命的余味”,她双手向前伸,想要抓住它。
她看上去像个可怜的布娃娃。我把她的白色蕾丝睡衣交给护士,母亲希望穿着它入殓。他们不想让我们做任何事。我想把睡衣套在她身上。
我再也听不见她说话了。
14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感觉她还活着。在面包店,在蛋糕面前,“我不需要再买了”,就像“我不需要再去医院了”。
想到《白玫瑰》这首歌,小时候听会让我流泪。现在听到,这首歌,我又哭了。
28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在一张账单上我看到一个词,“污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叫她“乌乌”。眼泪涌上来,那是因为时光。
节选自《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原文作者/安妮·埃尔诺
翻译/黄荭
摘编/黄荭 张婷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