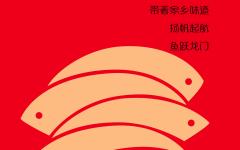尽管凛冬的寒风冻得嗅觉麻木,但鼻腔里依然能闻到过年的味道。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回家过年的返乡潮卷走了一座座办公楼里平日的人流,空旷的楼层里,昔日被咖啡香气遮掩的积年尘土味道,头一次能如此清晰地闻到。火车站中,山海般汹涌的人流,散发着南来北往的不同气味。焦香馥郁的腊肉味来自于楚山湘水之间,酱香浓厚的熏货则来自秦晋燕赵之地。簇新的衣服散发着第一次与人体接触所特有的青涩味道,车厢里的泡开的方便面和着被暖气蒸腾的鞋袜汗水,散发着一股特有的酸香。
如是说来,年味儿与日常的味道并无不同,只是过年的信号,将平日习以为常的味道放大了百倍千倍。但年味儿不仅仅限于味觉与嗅觉,它并非具体的某种味道,而是一种眼耳鼻舌身意的通感。关于这一点,早在一个世纪前,一份著名八卦小报《北洋画报》就对年味儿有了精辟的定义:“年味,盖不仅指口之所触而言,凡耳闻,目睹者,亦皆属之。吃年糕,饮屠苏,年味也;闻爆竹声,空竹声,年味也;见穿红衣之小姑娘,关公读书之年画,亦年味也;然须三者兼之,方觉年味浓厚”。
年糕、屠苏酒、爆竹、空竹、穿红衣之小姑娘与关公读书之年画,一个世纪前的年味儿代表,虽然世殊时异,然而余味儿依然悠长,至今依稀可闻——过年本就是这样,平日里沉睡的古老灵魂,借着过年的时候复苏过来,将古老又古老的色声香味,寻空插隙渗进此时此刻的当下,也只有在此时,那些来自古远的味道,才显得不那么突兀,才显得如此自然而然,宛如这年味儿原本就一直徘徊在这里,只是在那过去忙碌而嘈杂的十一个月里,偶尔遗忘了,直到此时此刻,才又闻到了那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千百年来酝酿出的熟悉的年味儿。
磨豆腐

磨豆腐。图片出自《年味儿》。
提起年味儿,总是让人想起杀猪宰羊的荤腥味儿,过年的宴席上,煎炒烹炸的各种肉食,自是必不可少。但尝尽了肉食滋味,素净的豆腐,最是能涤荡挂满了油水的肠胃。
“腊月二十五,家家磨豆腐”,这句俗语着实不知从何而来,因为吃豆腐似乎是一年四季的事情,算不上大典。豆腐坊也随处可见。磨浆的磨子、卖浆的锅、吊浆的布兜,都干干净净。盛豆腐的木格刷洗得露出木丝。什么东西都好像是新置的。”汪曾祺笔下豆腐坊的场景,至今在一些小城中依然得见,只是大多数豆腐坊屋子里都是黯淡的光景,四壁黑魆魆的,除了做豆腐的器具被豆腐水日复一日刷洗得干干净净,算是豆腐坊里一抹亮色。好的豆腐坊,清晨路过时,总能仰鼻闻到一股子热腾腾的豆香味儿,混着微微发酵的豆腥,像夏日的雨后一般清新而温暖。豆腐吃起来,也颇为简便,切小葱加细盐,便是一道能上台面的清口菜。即使是用水白煮,也是入得了名家法眼。一如朱自清笔下儿时冬日里的白煮豆腐:
“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
豆腐是穷苦大众的恩物,但出身却被攀附到了那位传说鸡犬升天的汉代皇族贵胄刘安身上,多少有些令人慨叹。其实这说法,不过是来自南宋朱夫子《豆腐》诗中的一句话“早知淮南术,安生获泉布”,并无更多确凿的实据。河南密县打虎亭村东汉墓中发现的画像石上庖厨场景,被有心的考古学家解释为豆腐作坊,说图中浸豆、磨豆、滤浆、点浆、榨水几个主要过程一应俱全,只欠煮浆一个环节。这似乎离着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传说迈进了大大的一步,但无法解释为何自汉至唐数百年来,豆腐从未见于任何记载。直到五代宋初,才在《清异录》中露了一面。但无论豆腐出身为何,生于何时,它如今已成为大众最日常的饮食,一道豆腐,可与百味搭配,上至鲍参翅肚,下至青菜韭葱,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冬日里的冻豆腐,更是借了凛冬寒气,变得更加耐人寻味。晚清文人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言冻豆腐“得味外味焉”,所言甚是。
忽而想起几天前,正是临近春节的凛冬黄昏,路过菜市场时,见豆腐坊摆出来的豆腐,在寒风中放了一天,竟然外面也冻上了,里面犹是嫩豆腐的凝脂玉体,外面却已然是蜂窝满布的老皮老脸,辞旧迎新之况味,豆腐亦复如是。
舞狮子

舞狮子。图片出自《年味儿》。
舞狮子一直有种让人滑稽想笑的感觉,那么大的头,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嘴巴也一开一合,分明一副憨态可掬的样貌,却又有着痩条的身子,上蹿下跳,如许灵活,当真是狮不可貌相。比起动物园中总是懒洋洋晒太阳的所谓百兽之王,舞狮子更有活力,更有人情味,更能让人感到欢愉——似乎它原本就是为了让人笑而诞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舞狮子在中国的起源,确实是一种娱乐,无论是《汉书·乐志》中提到的宫廷乐舞中的“象人”是不是曹魏孟康在注释中所说的“若今戏鱼、虾、师子(狮子)者也”;还是《洛阳伽蓝记》中洛阳长秋寺佛像出行时,有“辟邪、狮子,引导其前”,都足以证明,舞狮子是在乐舞游行中带来欢愉效果的表演。到了唐代,狮子舞更是盛行一时,《乐府杂录》把狮子舞列入龟兹部,唐代立部伎中的《太平乐》即根据《五方狮子舞》改编而成,成为上百人集体表演的大型乐舞。《通典》中记载的“五方狮子舞”更是欢乐非凡,五头狮子分青赤黄白黑五色,由一百四十人围绕狮子“歌太平乐舞”,宏大而热烈——狮子舞惹人欢笑,自是自然。
“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娱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长在目”,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如此描写封疆官将对狮子舞的乐此不疲,但在笑闹酣醉的乐舞欢宴中,他却将目光落在了一个年已七旬的普通士兵身上,如此欢乐的狮子舞并未让他一同发出笑声,反而是低面而泣。因为这看似欢乐的狮子舞,讲述的却是一段边疆哀史,那“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的“假面胡人假狮子”,实际上正是当年凉州尚未陷没于吐蕃时,安西都护进贡给长安唐廷的最后几头狮子,当他们行在半途,却听闻了凉州陷没的消息:
“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
故土沦陷,有家难回的泣泪悲剧,就这样被演绎成了一出让人欢笑的喜剧,这恐怕也是身处历史尘沙中的胡人与狮子所未想到之事。不过历史的尘沙自然能掩盖哀叹泪水,中国的传统也能用遗忘将悲泣替换成喜极而泣。七个世纪后,身逢明清易代之际的顾景星,发现湖北蕲州居然还在上演这场时空远隔千载万里的唐代狮子舞,只是与当地的傩戏融为一体,表演者“著黄袍、远游冠,曰唐明皇,左右青面涂金粉、金银兜鍪者三,曰太尉”,周围环绕着数十徒众,“列幛歌舞,非诗非词,长短成句,一唱众和”,不久,有两个人持碟上前,一只由人扮演的大狮子“首尾奋迅而出”,蛮奴问狮子从何而来,答道“凉州来!”于是“相与西向而泣”。
“千秋事已往,此舞胡为乎?”看完这场狮子舞后,顾景星发出如是感慨,昔日愉悦晚唐将士的乐舞,如今又博得明末士民欢笑,传统就是有着如此强盛的生命力。
今天观看狮子舞的人,不会有人追寻狮子舞的古老故事,毕竟时间有着淡化一切的魔力,唐代沙尘,明代烽烟,终归都已经被时间扫却,只有那历史传来的欢快笑声,宛如舞狮子的面具一样,活灵活现地装点在每一张年味儿十足的欢乐脸上。
放爆竹

放爆竹的孩子们。图片出自《年味儿》。
爆竹是一种神奇的物什,仿佛天然洋溢着一种孩子气,放爆竹是小孩子过年时最喜欢的玩乐,纵然是大人,点燃爆竹时的躲闪跳跃,又活像个小孩子,暗夜中红色黄色连绵不断的火光,噼噼啪啪地闪动着,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是一股孩子气的笑容。空气里散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弄得人鼻子一耸,更像是个孩子。
说来也是怪哉,爆竹的初衷,本是极严肃的仪式。南朝梁宗慷《荆楚岁时记》大抵是关于爆竹最早的记载,正月初一那天,“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所谓的“山臊”,根据《神异经》中的记载,乃是西方深山中一种身长尺余的一足袒身小人,这种小人“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入不在,而盗入盐,以食虾蟹”。
明明是山臊主动侵扰人类,但是人类如果反击它,却“犯之令人寒热”。爆竹是唯一能够驱赶它的法宝,“人以竹著火中,爆扑而出”,山臊便会“惊惮”。
如此恶鬼,只要爆竹的响声便可以轻易驱离,随着火药发明,噼啪作响之声,更胜过以竹著火中发出的声响百倍,想必这种山臊恶鬼恐怕连肝胆都要被震碎了吧?
虽然古籍中对山臊恶鬼的描述仿佛确有其物,而后世笔记野乘又乐于添油加醋,让它的形象由独脚小人,变成猴面人身,再转化为江南地区俗信的五通神,但它的本质,恐怕并非是恶作剧的小人,而是犯之令人寒热的瘟疫。
先民或许正是观察到了某些可以由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瘟疫,因此想到了用焚烧爆竹的响动来驱赶野外动物的方法。毕竟,对古人来说,凛冬季节本就是最难熬的时节,冬春之交,正是瘟疫易于流行的时候。秦汉时期在腊月举行的大傩,穿着玄衣朱裳,披着熊皮,戴着黄金四目的面具,执戈扬盾的方相氏,便是人类为驱逐瘟疫恶鬼而创造出的鬼神,用比疫鬼更可怖狰狞的面目来吓跑疫鬼。大傩仪式上的方相与元旦燃放的爆竹用意相同,只是一个用面孔,一个用声响。《月令广义》所谓“除夕爆竹,所以震发春阳,消除邪疠”,正是此意。

《年味儿》,保冬妮、于洪燕著绘,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贝贝熊童书馆,2021年1月。
《月令广义》已是明人的著作,但自唐宋以来,逮及明清,爆竹早已脱去了惊吓山臊的初意,成为了一种过年的习俗。从宋人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到清人的“一声爆竹除残腊,换尽桃符逐祟回。 且缓屠苏守岁饮,听他万户震天雷”。爆竹也从往火里放几根竹子,变得花样繁多,晚明《宛署杂记》记载燕京爆竹种类,即有“响炮起火、三级浪、地老鼠、沙锅儿、花筩、花盆诸制”,争奇斗艳,不光是听声响,更有炫目烟火,在耳鼓间震动,在瞳孔中摇曳。
爆竹,是喧嚷的,就像汪曾祺笔下的故乡阴城的那场烟火盛会“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抑或是鲁迅《祝福》中故乡鲁镇的爆竹,“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震动天地的声响,衬托着那个融化在万千因年味儿到来而欢笑喜乐的喧嚷中小小身影,仿佛这爆竹声响过,真个是与旧时告别,投入新年的怀抱。但时间流逝自古至今,并不会为这人造的震天声响而割断,一如昨日的脚印会被夜雪覆盖,但今天身处的此处,却已证明了走过的道路。
“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作者/李夏恩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