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十月底的一个阴雨天,早早赶去橘园美术馆看莫奈的《睡莲》,没想首先看到的是在门口排起的长队。进厅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人或坐或站,专心观察着墙壁上巨大的画作,那时,即便开口说话似乎也是沉默的。这些人在看的是什么?是莫奈用生命捕捉到的光影与色彩。
莫奈说,“光是画面上的主要人物”。这些光,也让诗人王璞深深着迷。在今天推送的文章中,王璞从莫奈的画展开始,跟随光影,进入莫奈,进入记忆,进入自己,最终有所悟般怅然:“莫奈和我们,本该是光的开放和在地。”

克劳德·莫奈(1840年11月14日-1926年12月5日),法国画家。被誉为“印象派领导者”,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图为莫奈《戴着贝雷帽的自画像》。
睡莲,池塘,谷垛,开着野花的草地:一幅幅莫奈画作,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展厅中挂起。那是2020年底到2021年初,美国疫情的深深处,计划外的“莫奈和波士顿”特展,网上预约,定时分流入场,无接触检票,参观必须佩戴口罩。

莫奈《睡莲》,1907。
克劳德·莫奈是印象主义绘画创始人之一,他创作生涯长,作品数量巨大,在北美流布甚广。看展经年,我甚至会有一种感觉:有点分量的美国博物馆,哪家没有一幅《睡莲》睡在墙上或库房?那么,波士顿美术馆的疫期特展,立意又在哪儿呢?它要追溯莫奈和波士顿极早的缘分,那是莫奈和法国印象主义在美国受到追捧的开始;它要展示波士顿人士从莫奈还在世时就收购他的作品,更持续不断,形成了一份巨大的印象主义宝藏。
波士顿算得上美国的“衣冠文物”盛地,也是美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和欧洲文化隔海而又相连。波士顿的上层名流,在老欧洲眼中是新富,在新大陆则可称“老钱”,早在1883年就让莫奈的作品跨过了大洋,那时,美国文化公众对印象派还缺少感觉,只对它在自己祖国的遭遇略知一二。莫奈友人们也没对波士顿博览会上的展出抱太高期望。不过,1891年,波士顿美术馆就已专门租借莫奈作品来展览。而到了1926年莫奈辞世时,波士顿的纪念文章已在列举望族的私藏和波士顿美术馆的购置,认为流入当地的莫奈作品“难以计数”。时人更以为,“波士顿人最早看到这位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的最长久的纪念之一便是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看来,法兰西的莫奈之光早已越过大西洋,在新英格兰的名城闪烁变幻,也正如展览副标题所指,这的确可谓“持久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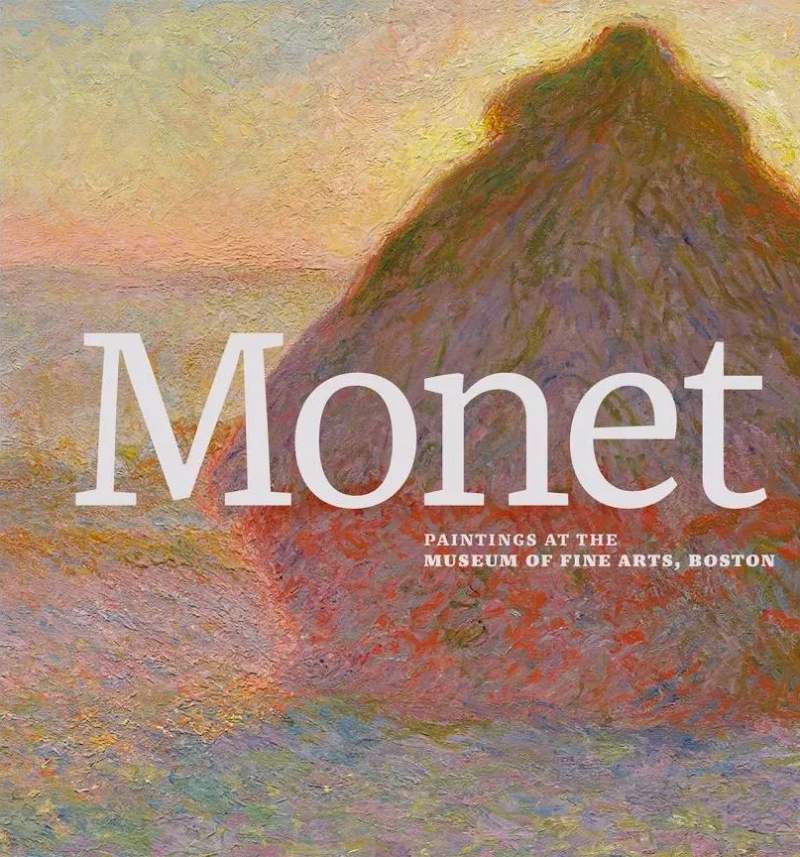
画册《莫奈和波士顿》。画册封面为莫奈画作《干草垛》。
铁路的铺设和普及,新兴阶级的户外和郊游,城乡间人的流动和交通,这一切,造就了印象主义的色彩和阴影,在十九世纪法兰西最明丽也最隐晦之处,Plein air(外光绘画)的时刻真的来了!
莫奈在法国各地反复描摹着光:莫奈之光是枫丹白露和巴黎周边小站的雪景,是诺曼底的孤树和海岸,是地中海昂蒂布的晨昏,是克勒兹省的山色……原本,波士顿美术馆就常设“莫奈厅”(展厅252),而因为新冠大流行,跨国策展忽然变为不可能,特展索性把历史上收藏的莫奈光影都翻腾出来放在一起,构成法兰西四时印象,就像一百多年前一样,重新训练我们的眼。这些集中展出的画作,有许多地名,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特别牵动我的记忆,那便是吉维尼(Giverny)。

莫奈《吉维尼的日落》,1886。
吉维尼是法国诺曼底大区厄尔省的一个小镇,在塞纳河下游右岸,距巴黎西北方向不过80公里。1883年,莫奈搬至吉维尼,在此生活43年,直至去世。这座小镇是莫奈人生的落脚点,也由此成为印象主义又一处光源。莫奈反复画这里的草坡野花,反复画塞纳河畔的晨曦,我尤其喜欢他画镇外的谷垛,那真是光的练习,从日落时谷垛超出玫瑰色的红,到谷垛在雪地上留下的幽蓝倒影。当然,莫奈也画庭院,院中的妻子,也画池塘,池塘上的桥,水中的睡莲——那里的一切在1970年代得到了修缮,现在是“莫奈故居和花园”博物馆。2021年,在波士顿的展厅中面对这些上百年但依旧鲜活的色彩,我不禁想起来自己十多年前的吉维尼之旅。
2008年秋,我还是纽约大学博士生,到法国访学一学期,纽约大学巴黎校区安排研究生开学培训,就选在了吉维尼。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法国,巴黎在初秋阳光下的金色仍让我眩晕,我就得到了郊游的印象主义机会。
学校租用的别墅离莫奈故居不远,中间穿过几片草坡和草地,可惜没有莫奈画过的野花,旁边砂石地上停着美国、日本、韩国旅行团的大巴(中国游客那时还没能占领这好地方),尤其是一大群美国的中学生,傻傻地胡闹着,总是那么好辨认。来到莫奈的疗养别墅,我终于领略到法式窗扉的美,那绿色!进入室内,我却很快感觉到莫奈画室的日本风。的确,莫奈崇尚日本艺术,也算引领法国的日本风的人物吧。在2021年波士顿的特展中,最大幅的作品便是莫奈画妻子穿着和服拿着扇子模仿日本舞动作,这幅画既是人物又是室内,再加上近乎真人比例,放在许多较小的风景印象之中,特别引人注目,也是波士顿美术馆历史上对莫奈作品最重要的收购之一。再回到2008年,当我移步花园,日本风又在室外展开。我当时对日本园艺在法国的影响还不甚了然,后来,我将遇到许许多多法国的日式花园。莫奈画中反复出现的园中小桥,不正是日式的吗?我的记忆和波士顿特展中的作品不经意间联动了。

莫奈《穿日本和服的卡美伊》。
莫奈在吉维尼绘画几十年,而大多数游客只在这里一日游,看完故居和花园,不过夜便回巴黎。这已成为当地旅游业定律,以至于当时旁人听说我们这帮学生要在吉维尼待周末三天,都感到小小讶异。2008年和我同行的是一批美国女生和一位北非男生,我是法语最差的,因此选修不了法语课程,开学培训中的许多活动,都不用参加。这下落得清闲,我可以好好探访一番。
我倒没有早起去看“塞纳河的早晨”,也不知道谷垛是否可以寻到。可是正赶上法国的“文化遗产周末”,许多有历史的民宅和别墅都免费开放,我骑着自行车一户一户地看过去,多少漂亮的窗啊,在九月的正午,小巧而耀眼地敞开着一个世纪的心!转天早上,女同学们又推荐我去寻访莫奈墓。我骑着自行车,记得是缓坡山路,从故居再往西。树木迎着太阳,但当天时晴时阴。原来莫奈就葬在当地的教堂墓园。它是再普通不过的样子,也是我拜访的第一个法国墓园。一排墓碑如此安静、如此谦逊地映衬着蓝天。该如何形容(绘画)那种蓝呢?那是我还没有发现azure(天蓝色)是十九世纪法语诗歌中的常用词。忽然云又来了,莫奈墓前的丰富花草收敛了一些艳丽,却也并未完全归入沉郁。

莫奈故居。
我的记忆中只残留了这些印象。当时我带了一部尼康FM2机械相机。借助老照片,我依稀想起在吉维尼的最后时辰,我和北非同学散步,拉出越来越长的影子,聊了些什么?和他后来也失去了联系。那落日的光,多么浓烈,又多么通透,吉维尼多少只窗瞬间饱含最为明亮的泪?那光,也正是莫奈画谷垛时所研习的光吧?或者说,那不是莫奈在练习光的绘画,而是光在练习。光在练习着时光的印象。
离开吉维尼,我忙着开始三个月的穷学生都会生活,虽然在美术馆中不断和莫奈重逢,那光的练习很快被巴黎的忧郁之冬所淡化。不久后也有机会去鲁昂看了莫奈反复画过的大教堂,他一次次表现光的变化,可惜我那一回只是一个阴沉的冬日,无从有光的练习。
没想到,疫情期间的特展,却复活了我记忆中的印象,让我从波士顿回到吉维尼。这也是莫奈之光的练习吧?我始终不喜欢波士顿美术馆展厅的昏沉,不过,在美国疫情的绵延处,参观者置身其中,也算共沐于莫奈之光。我也不禁怅然:莫奈和我们,本该是光的开放和在地。现在,特展也已过去两三年。现在,是重新开放的时候了。我翻着《莫奈和波士顿》的画册,不知何时能重游吉维尼、重访秋阳下的花园和墓园?至少,还有记忆中不断苏醒的印象,总可以重新开始光的练习——我们和莫奈,应是记忆和光,应是记忆中光的印象和练习。

莫奈《日出·印象》。
撰文/王璞(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
编辑/张进
校对/柳宝庆 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