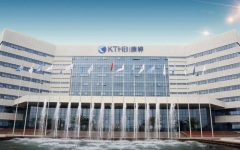在第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一批2023年下半年以来出版的知识产权精品图书,其中,律师赵俊杰的新书《船长说版权》被列入“知识产权实务用书”。
在这本书中,他一人分饰多角:以律师、仲裁员、调解员、项目评审、公益普法人、园区创业导师、人才甄选面试官、版权知识竞赛评委等身份,从不同角度与读者分享办案思维方法、企业管理体系构建、大学生法律职业生涯规划,并通过充满烟火气的人文现象等多元视角,展现了客观真实又蓬勃发展的中国版权与人文法治图景。
赵俊杰在法律实务一线尤其是版权法领域,已开展实践与研究超过20年。他有多个身份:执业律师、仲裁员、司法鉴定人,在业内,多地同仁亲切地称其为“船长”——他常年坚持公益普法,主理举办各类法律与知识产权研讨会超过300场。

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赵俊杰(右)新书《船长说版权》作为捐赠文献入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受访者供图
他同时也是《新京报》的老朋友。2014年,他应《新京报》约稿,撰写了一篇题为《新媒体“拿来主义”的界限何在》的时事评论,原本是提醒新媒体不得随意“拿来”,谁知该文章发表后几小时内就被转载超过15万次,用赵俊杰的话说:“成了不折不扣的版权笑话。”他的这个案子,也成为新媒体侵权的一个经典案例。
版权与著作权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人说版权法是一门法律“玄学”?面对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我国现阶段版权保护面临哪些困境?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存在哪些问题?针对诸如此类的版权领域热点问题,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赵俊杰,他表示,面对版权“拿来主义”困境以及人工智能布局的迅猛推进,要在短期内寻得行之有效的突破方法恐怕还有困难,需要更多坚守的人。
普及知识产权法需要更多热心的“船长”
新京报:为什么大家都叫你“船长”?
赵俊杰:一提到船长,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波澜壮阔的大海。当船遭遇巨大灾难之时,船长应当最后一个离船,“与船共存亡”。濮存昕在其所著《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一书中,把船长的品格描述为“不向挫折低头”。
十几年前,在北上广等地的知识产权圈,出现了一批深耕一域、热心普及知识产权法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知识产权-学术没有圈”、洪波维奇、“村长”、馆长、“乔帮主”、船长(Jack 船长、杰克船长)等人。多篇文章对我带领同仁在多地进行公益普法做了报道。其中,知产力《对话 IP 人 丨赵俊杰:听船长畅谈我国版权事业那些事》一文提及,我既具有舵手的品质,又持续深耕版权,业内同仁都称我为“船长”。
勇敢、智慧、担当、值得托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船长印象。应该说,这恰恰是我须长期追求和锻造的品质。我认为,普及知识产权法,还需要更多热心的“船长”。
新京报:《船长说版权》这本书,你酝酿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想到出一本这样的书?
赵俊杰:印象中有这个想法超过6年了,后来还成立了专门的撰写工作组。但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启动。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现在的责任编辑李陵书老师。她严谨、专业、高效的工作方式,促成了本书的付梓。
由于工作涉足的领域与文学、影视有密切关系,我本人也参与一些地方的电影、音乐创作及维权等工作,而知名民商法公众号“高杉LEGAL”一贯主张“写作,是专业上获得成长的最好方式”,以及马贺安律师所著《生存与尊严》一书提出演讲和写作是“教导式展业”(非“兜售式展业”)的有效方法。因此,出一本书、拍一部电影便成为我的两个梦想。
新京报:经常有人问我,版权和著作权是一回事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赵俊杰:版权是法律的一个分支,对作者(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创作者)的作品给予保护。其起源是与15世纪欧洲印刷术(谷登堡印刷机)的发明相联系的。在法治实践场景中,“版权”通常与“著作权”作为同义语使用,并未作严格区分,比如人们常说“版权产业”“版权登记”“数字版权”等。我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明确界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
新京报: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到很多研究知识产权、版权领域的律师,常听到有人说:版权法是一门法律“玄学”?为什么这么说?
赵俊杰:我印象中,最早郑成思教授曾说,著作权法是鬼学和玄学,就是指著作权法的权利体系或逻辑原理异常复杂。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著作权法》不过如此,也就60来条,可是当你逐步接触具体案例、开始论证某个学术观点时,会感到吃力。再后来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总体来说,对于版权法及延伸领域的学习工作感受,很难用“一是一、二是二”进行概括,不少问题包括追续权、孤儿作品、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版权“拿来主义”困境短期内破局有困难
新京报: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版权纠纷的“重灾区”。面对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你认为我国现阶段版权保护面临哪些困境?该如何突破?
赵俊杰:我国现阶段版权保护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第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律具有滞后性。第二,司法既要保护新兴产业,又要尊重创作者,有时候很难取舍。第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其他效果,如何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予以平衡。我认为,面对“拿来主义”困境以及人工智能布局的迅猛推进,要在短期内寻得行之有效的突破方法恐怕是困难的,还需要包括律师在内的更多坚守的人。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新京报: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的争论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存在哪些问题?
赵俊杰: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4月25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中国软件知识产权保护高峰论坛圆桌对话中,嘉宾们专门对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我认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许是:司法执法如何在原始创作人权益和通过训练素材加特定规则生成新素材的群体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2023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在业界引起广泛讨论;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罢工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创作与保护的思考。AIGC(AI Generated Content)相较于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其创作方式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面临素材原始权利人的苛责。
新京报:十年前,你在《新京报》上首发《新媒体“拿来主义”的界限何在》一文,呼吁新媒体不要随意拿来,结果却成为了一个新媒体侵权的经典案例。十年过去了,你认为我国的版权保护有哪些进步?
赵俊杰:我当时写这篇文章原本是提醒新媒体不得随意“拿来”,没想到文章在《新京报》上发表后,仅几个小时内,就被转载了超过15万次,没有一个人联系我支付稿费,这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版权笑话。说实话,那时我惊呆了,为什么主题为新媒体不能随便“拿来”的评论,仍然逃不掉未经许可被大面积转载的局面?随后我就委托律师起诉,积极开展维权,审理法院就行为人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该案后来也引起多家媒体的关注并被刊发报道。
十年过去了,如今,经授权使用他人作品的理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听歌还是看电影,都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先付费后使用的做法在平台、创作者、消费者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在一些新兴领域,比如AI作画与GPT问答,人们对训练素材的可版权性认识、对科技与版权错综复杂的关联较以往苛以更高注意义务的做法,侧面上就印证了这一点。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陈静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