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博
摘编|徐学勤
1947年,当《鼠疫》在法国正式出版之时,加缪本人并未亲身经历过任何一场大范围流行病。他关于鼠疫的全部病理细节,无不来源于医学文本与历史资料中的二手经验。
他在小说的筹备阶段对这些文献的收集和研读颇下过一番苦功,这最终使他的相关措辞与描述显得极为专业。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性全面而深刻的洞察令他恍若身在现场。他的笔触遍及官僚、记者、医生、病患以及民众,他们或悲壮或卑微,或可敬或可笑,或理智或疯狂,或为公益或为私利。加缪告诉我们,什么人在互相推诿,什么人在担起职责;什么人在钳制舆论,什么人在启发民智;什么人在传播谣言,什么人在澄清事实;什么人在畏葸逃避,什么人在前线奋战;什么人不顾他人安危肆意妄为,什么人以生命为代价发出预警。加缪试图证明:众生喧哗之中,并非所有人都只顾个人的安危甚至舒适。他的目光关注每一位无名的抵抗者,不只驻守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那些负责统计数据的文员、看管营地的门卫、自发组织的护工等,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构筑起一面人类最坚强的抗疫之盾。在这些伟大逆行者的背影中,加缪为我们展现了人性之光的高贵与璀璨,并且告诉我们,“在人类身上值得赞美的比应当蔑视的东西更多”。
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鼠疫》。甚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携带着现实经验进入这部小说。相信加缪本人对此也会深表赞同。因为这代表着我们通过阅读文学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穿过小说的虚构透视我们真实的人生,去追问生命的真谛。《鼠疫》的象征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话》等。
从荒诞到反抗:一场由鼠疫引发的人类行动
如若要从《鼠疫》中提取几个关键词,那么“荒诞”与“反抗”必定位列前茅。“荒诞”化身为一场致命疾病大发淫威,而“反抗”则由无数人的抗“疫”之战共同呈现。它们并非小说的唯一情节,分离与流亡、彼岸与此世、个人幸福与集体责任、爱情的真实与虚幻,乃至于写作的可能与不可能等,这些丰富的内容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庞大的精神世界。这不是一部由纯粹思辨构成的哲理论文,而是一部“铭刻在现实的厚度之内”的文学创作,所以本不应该提取什么关键词,因为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意义就越是沉浸在细节中。上文提到的每一个话题都理应获得重视和探讨。不过,小说毕竟存在一条主线:一场由鼠疫引发的人类行动。或者更加粗略地简化为:一场由荒诞引发的反抗。我们需要牢记这只是一种粗略的简化,它完全不能代表小说的全部,但我们的研读依然选择从这里落笔。
无论“荒诞”还是“反抗”,在加缪的思想世界中都是超越单一作品之上的纲领性概念。所以,它们在加缪笔下必然有其来龙去脉、起承转合。为了厘清《鼠疫》中的“荒诞”和“反抗”,就不能局限于这部小说的内容本身,必须引入其他作品加以参照。一方面,这让我们可以追溯《鼠疫》中反抗思想的来源并看到它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加缪的许多论述性文字和小说在思想性上互为表里,比小说中迂回的表达更加直接明确。它们是理解《鼠疫》中反抗思想的必备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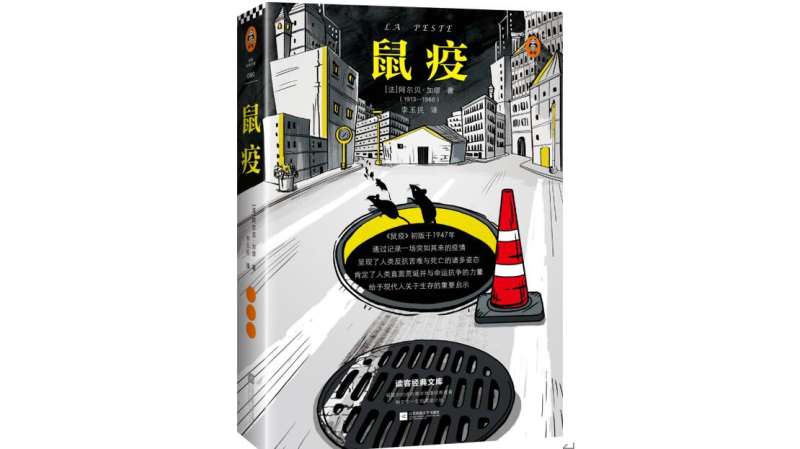
《鼠疫》[法] 阿尔贝·加缪著,李玉民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在加缪笔下,“荒诞”与“反抗”这两个关键词,在写作《鼠疫》之前都已出现。前者毋庸多言,“荒诞”早已和《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卡里古拉》这些“荒诞系列”作品紧紧绑定在一起。相比之下,加缪的早期作品中论及“反抗”的篇幅较为有限,但并不因此而缺少重要性。面对世界与人生的荒诞,加缪从一开始便清晰地感到人不能因此屈服,需要去寻找一种方式反抗这种处境,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重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意义”抵抗“无意义”,这便是加缪反抗思想的最初起源。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的《荒诞自由》一节,加缪第一次提出了“反抗”的内涵,他写道:“反抗将其自身的价值赋予生命。它延展在生存的完整始末,恢复了生存的伟大。对于眼界宽广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美景能够超过智慧与一种使人不知所措的现实的搏斗。人类的自尊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景观。一切贬低在此都将毫无意义。这种精神自律的守则,这种由万事万物锻造而成的意志,这种直面的态度,这其中包含着某种强大而独特的东西。现实的非人性造就了人的伟大,削弱这种现实,也就同时削弱了人自己。”
加缪不回避现实的“非人性”(“荒诞”的同义词),但他强调人类需要对此现状彻底地加以认识,承担这种认识所带来的重压,并最终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寻找价值的动力。承认一种无法逃避的沉重现实,但不承认人类在这种现实面前注定被“荒诞”同化,这便是加缪借用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这个形象所象征的内容,也是他在此处赋予“反抗”的含义。对于每一个在柜台、办公室、流水线或其他地方从周一工作到周五的普通人,我们从某种程度上都生活在一块永远推不完的巨石面前。这是一种困境,加缪将其视为“荒诞”的表现形式之一。面对荒诞,加缪“渴望知道是否可以义无反顾地生活”,追问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世界的荒诞无法消解,或者说荒诞本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块巨石等待他去推动,人生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加缪恰恰在此时说道:推动巨石,忍受这个荒诞的世界并不代表屈服,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清醒过来,看到我们荒诞的处境以及我们注定失败(死亡)的结局,我们便看清了自身的局限,同时知晓人生的意义既不来自上天也不来自彼岸,它仅来自人,必须由人本身来创造,也只能通过人来创造。对自身的处境拥有冷静的认识,保持反抗的灵魂,守护心灵的独立,将巨石一次又一次推起,在加缪看来是一件英勇之事。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用人类的双手创造意义,这就是写作《西西弗斯神话》时加缪眼中“反抗”的使命与内涵。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西西弗斯神话》与《局外人》一样,讨论的是普遍性的日常,于是这块压迫西西弗斯的巨石始终未被打碎,加缪对于西西弗斯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承认这块巨石存在的基础之上。因为在当时的加缪看来,这块巨石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谓其固有属性:“现实的非人性造就了人的伟大,削弱这种现实,也就同时削弱了人自己。”所以,他没有让西西弗斯把反抗引向这块外部的巨石,转而激发内心不屈的意志。西西弗斯由此可以被称为“内心的反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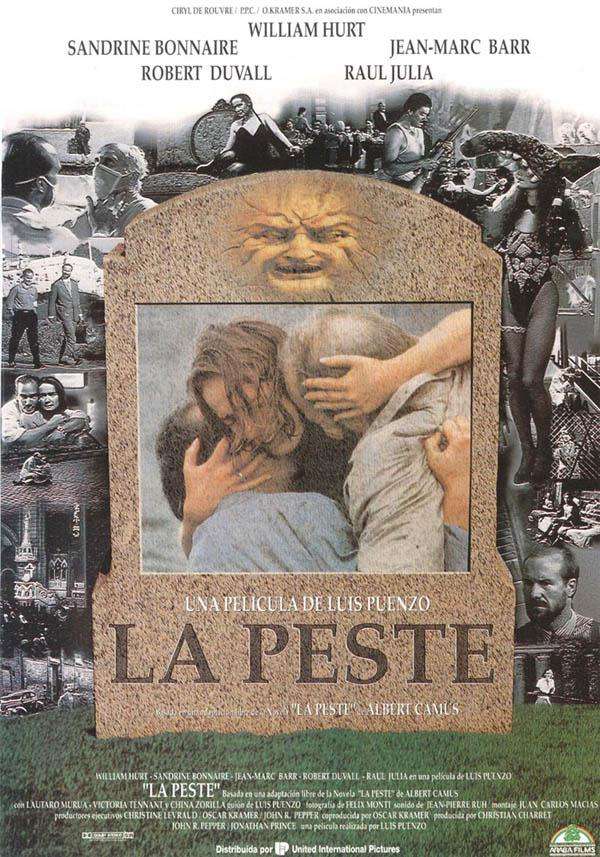
1992年,根据加缪《鼠疫》改编的同名电影海报。
然而,1939年9月爆发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外部环境。世界不再仅仅是无意义的荒凉,它正在被人性的黑暗、残忍的吼叫与绝望的哀号所覆盖,荒诞已不仅是一块推不完的巨石,它还变成了一架血肉无法填满的杀人机器(鼠疫)。在这样的境况面前,加缪拒绝承认现状,他要打破这一切非正义,于是,西西弗斯式的内心反抗转变为一种全面的行动。《鼠疫》的诞生亦肇始于此。他决定起身砸碎这块巨石,这对于加缪而言是一个关键节点。战争爆发不久后,他在《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独白:
试图与世隔绝永远是虚妄的,哪怕是为了隔绝他人的愚行与残酷。我们不能说“我不知情”。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挺身应战。没有什么比战争及挑动民族仇恨更不可原谅。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以事不关己为借口试图置身事外是虚妄和懦弱的。象牙塔已经崩塌。无论对于自己还是他人,都严禁逆来顺受。
从外部去评断某一事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唯有在这荒诞的灾祸内部我们方才保有蔑视它的权利……我身处战争之中并且我拥有评断它的权利。加以评断并展开行动。
这则笔记清晰地预示,加缪抗拒“与世隔绝”,并将在战争中“展开行动”,他将离开崩塌的象牙塔,走向更广泛的人群。这将成为其人生中一个新的阶段,亦将构成包括《鼠疫》在内的加缪“反抗系列”真正的基础。加缪的这段自白应该被视为他1941年4月决定创作《鼠疫》的一个重要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不仅构成了《鼠疫》创作阶段的历史背景,也是一个深刻的刺激,使他意识到走出个人孤独艺术天地的必要。

西班牙电视剧《黑死病》剧照。
与之相比,西西弗斯作为“内心的反抗者”,更应被视作反抗思想完善前的一种前置性铺垫。当然,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反抗”被视为一种人类在无意义世界中寻找与创造意义的方式,这一点始终有效。“反抗”从根本上始终是一种重建价值的行动,它之所以在反对并打破着什么,是因为它首先在赞同与坚持着什么,这也是加缪从否定走向肯定的一贯方式。就像1945年他在《关于“反抗”的评注》开篇所说的那样:“什么是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但如果说他拒绝,他却从未放弃,所以他也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说‘是’的人。”这段话后来被他原封不动地放在了《反抗者》的开头,更可以被视作《鼠疫》的重要注脚——不要忘记,1945年加缪正在对《鼠疫》进行密集修改,这篇《关于“反抗”的评注》表达的内容与《鼠疫》堪称一体两面。理解这篇文章对我们澄清《鼠疫》中荒诞与反抗的关系大有裨益。
一个说“是”的反抗者,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重建价值与意义的人,西西弗斯传递了这一点,他对诸神说“不”,正是因为他对人类的尊严说“是”;与此同时,加缪也在不断赋予“反抗”更多的内容,它不但是个体自我寻找、自我探寻、自我构筑意义的过程,也同时呼唤着人类在共同的苦难面前携手共进。这也成为战后加缪每一次使用“反抗”一词时所同时具备的潜台词。在加缪1955年致罗兰·巴特的公开信中,他明确指出:“相比《局外人》,《鼠疫》无可置疑地指明一条通道,从一种孤独的反抗态度走向一种必须携手而战的共同认知。如果说存在从《局外人》向《鼠疫》的演化,它正是在团结与分担的意义上形成的。”这些关于“团结与分担”的说辞绝非事后追认。早在《关于“反抗”的评注》中,加缪就已经说明:“我们已经看到,在对反抗的确认中铺展开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它将个体从假定的孤独中拽了出来,并奠定了一种价值。”接着他进一步论证道:
因此个体并非仅仅为了他自己去保卫这种价值。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参与。正是在反抗中,人超越自我走向他人,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来,人类的团结具有超验性。
至少,这就是反抗精神迈出的第一步,它展开了一种深入这个世界的荒诞性及其表面的无意义性的深思。在关于荒诞的经验中,悲剧是个人化的。从反抗运动开始,它将产生一种集体意识。它是所有人的冒险。
加缪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将关于荒诞的经验与关于反抗的经验加以区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荒诞经验中所具有的反抗意识,而是想更清楚地对“反抗”加以定义与分析。同时它也是一条明确的线索,将我们从《西西弗斯神话》引向《鼠疫》里的里厄、塔鲁、格朗、朗贝尔与帕纳卢。

《黑死病》中因瘟疫而罹难的人被集中掩埋。
走出自身的孤独与个人逻辑的困境
1946年,加缪在《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鼠疫》应该是为某种集体激情塑形的首次尝试。”“集体意识”“集体激情”,在这类词汇中,加缪试图凸显的正是人和人之间团结与分担的必要。在《鼠疫》结尾部分,我们也能在里厄的感想中看到意义相似的表述。
从《鼠疫》和《关于“反抗”的评注》开始,加缪扩充了他笔下反抗的含义,把独自一人的内心抗争引向了一群人共同的全面奋战。从此刻起,加缪意识到,这种反抗将使一个人走出他自身的孤独与他个人逻辑的困境,他依然在为自己奋斗,同时与他人并为他人而战,而且这样的团结与分担不会缩减个体的独立。《鼠疫》中塑造的诸多人物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对于里厄这位故事的叙事者和战斗在第一线的救护者而言,他面对鼠疫所做的一切,都被他归结为“本职工作”——治病救人。他不关心宗教意义的拯救,只关心每一个病人的健康,因为唯有后者通过亲手努力可以触及。他没有华丽的语言,但从不缺乏实干。他是一个凡人,也有他的无奈和疲惫,但他以一种谦逊的方式坚持了下来。对他来说,抗“疫”是他应承担的责任。
格朗的抗“疫”行动比里厄更加悄无声息。这位政府的临时雇员,一个社会中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他在上班之余兢兢业业地统计着死亡人数,始终坚持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他参与抗“疫”,是因为他也想出一份力。正如里厄所说,无论媒体宣传与否,在那些光辉灿烂的英雄主义形象中,永远不会涉及这样的人。尽管无人注目,格朗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不用空话大话,只须力所能及。
至于朗贝尔,他追求个人幸福,为了远方的爱人,他殚精竭虑试图离开这座被封锁的城市。这是正当的追求,里厄亦表示理解。朗贝尔渴望爱情,因此抗拒分离,他急迫地希望与远方的爱人团聚,他对爱情的理解不是建立于观念,而是立足于感知,他因此拒绝抽象概念,强调肉身真实的接触。他拥有一套以肉身感性为基础的坚定世界观。他的转变特征分明,不是因为在理性上被说服,而是从塔鲁处偶然得知,里厄的夫人同样居于远地,而且身患重疾。这一相似处境引发的共情让他决定参与抗“疫”。感性触动是他行动的原因。
神父帕纳卢参与救护则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虽然他的第一次布道遭里厄诟病,但在目睹奥通幼子被病痛折磨致死后,他深受触动,于是在第二次布道中改“你们”为“我们”,号召所有人用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轻视个人安危的气概去体现上帝之爱。他以身作则,身处抗“疫”第一线,但直到临死之前依旧透露出对医护的冷淡。这对于帕纳卢并不矛盾,无私的献身和把自己交给了上帝,都是秉承上帝的意志。帕纳卢参与抗“疫”的理由,始终依托于宗教,是宗教思维。
塔鲁一出场,似乎已然彻底认清了自我。他在封城后就主动联系里厄,希望成立防疫组织,在他看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参与抗“疫”,只是为了内心安宁。就和早年反对死刑一样,他不忍看着生命逝去。与帕纳卢不同,塔鲁死前一直试图微笑,他在小说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里厄老母亲听到他在弥留之际说,“现在一切都好”。求安宁,于是得安宁。
五位主角,五种态度,一种行动。加缪以这样的方式证明,集体不会消灭个性。唯一的反例是科塔尔,因为他代表“荒诞”,是“荒诞”的化身。科塔尔的出场就是一场自杀未遂,接着在鼠疫流行阶段如鱼得水,而在疫情结束后,他惊恐地朝大街开枪。这些信息足以让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放弃反抗,被荒诞吞没之人。科塔尔是整部《鼠疫》中面对鼠疫唯一的投降者,甚至从内心深处对其保持欢迎与期待,最终成为鼠疫的帮凶。科塔尔既是鼠疫面前所有负面人格的代表,又象征着根植人性之中的懦弱和对荒诞的臣服,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如果说《鼠疫》的主线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场由荒诞引发的反抗,那么,加缪书写的重心则落在各个角色面对“荒诞”的不同态度以及走向“反抗”的不同方式(科塔尔代表面对荒诞不予反抗的这类人)。小说的其他一系列主题也完全依托于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一一展开。我们不能忘记,加缪关注的各类问题,最终都要回归人的属性,都要在具体的人生中得到验证。《手记》中,加缪在1942年8月曾做过这样一个构想:“小说。不要把‘鼠疫’放进标题中。而是诸如‘囚徒们’之类的。”所谓“囚徒们”,当然是指里厄、塔鲁、朗贝尔等被围困在鼠疫中挣扎求生的人。虽然加缪最终依旧把小说命名为《鼠疫》,但“囚徒们”这一备选标题的出现,已经足以说明《鼠疫》中的角色不仅是构成故事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是故事的主要内容。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著,金祎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
荒诞是贫瘠而残酷的,它只负责摧毁一切
《鼠疫》是加缪继《局外人》后正式发表的第二本小说,也是他从“荒诞系列”过渡到“反抗系列”的奠基之作。在《鼠疫》最初的构思和草拟阶段,加缪就明确意识到了这部正在创作中的小说与《局外人》的不同。在其1942年的两则笔记中,加缪做出了这样的自我剖析:
没有明天
我所思比我本人更伟大并且让我感到无法将其定义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某种朝向否定之神圣性的艰苦跋涉——一种没有上帝的英雄主义——最终成为纯粹的人。一切人类美德,包括面对上帝时的孤独……《局外人》是零点。《神话》也是。《鼠疫》是一个进步,不是从零走向无限,而是走向一种更加深刻、有待定义的复杂性。终点将是圣者,不过他也有他的算术值——和普通人一样可测。
鼠疫。无法从中脱身。在草拟中这次出现太多“意外”。必须紧扣构思。《局外人》描述了直面荒诞时人的赤裸。《鼠疫》直面同一荒诞时诸多个人观点的深度对等。这是一个进步,它将在其他作品中逐步明晰。不过,除此之外,《鼠疫》证明荒诞本身不教授任何东西。这是决定性的进步。
在这两段独白中,加缪对草创之初的《鼠疫》给出了同一个判语:“进步”(progrès)。《局外人》是零点,是原点,是起点,是“直面荒诞时人的赤裸”,而《鼠疫》则是从零点“走向一种更加深刻、有待定义的复杂性”,是“直面同一荒诞时诸多个人观点的深度对等”。这一“深度对等”便是上文所谓的“复调”。加缪试图在《鼠疫》中描绘诸多人物面对荒诞时的态度和行动,并从中发掘内在的共性,这一想法从他构思《鼠疫》之时就已经萌生;同时,他在构思创作过程中感到:“《鼠疫》证明荒诞本身不教授任何东西。”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不能从荒诞中得到任何教益或教训,而是说,荒诞作为世界与人生的一部分,它本身是贫瘠的、残酷的、冷漠的,它不会主动给出任何教导,它就像鼠疫一样只负责单方面摧毁。
教益来自人,来自面对荒诞时人的态度与反应,来自接触荒诞后人对自身行动的判断和反思。所以,指明“荒诞”存在的下一步,最紧迫的不是继续解析“荒诞”本身,而是思考作为人应当如何思考和行动。加缪所谓“决定性的进步”正指向这一方向。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思考人在彻底摆脱诸神的情况下得到生存尊严的可能性,是人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生活并且创造出生活的意义。所以他会说:“终点将是圣者,不过他也有他的算术值——和普通人一样可测。”在这里,圣者(saint)完全脱离甚至翻转了传统的宗教意义,回归普通人(homme)的属性,宗教性至此完全解体,转化为道德性和伦理性,是人对神、人性对神性的胜利,或者用加缪在这则笔记里的话说,“一种没有上帝的英雄主义”,“最终成为纯粹的人”。人,始终是加缪密切关注的对象。《鼠疫》的核心意义不是描述鼠疫本身,而是呈现与之直面的人类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展开行动。这一系列构思最终在《鼠疫》中得到了实现。
在《鼠疫》结尾的一片欢庆之中,里厄提醒自己,以鼠疫为象征的“荒诞”不会彻底消失,无论对于世界的疯狂还是内心的阴暗,人类都不可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以里厄为代表的反抗者始终保持着警惕。从长远看,鼠疫依旧如同西西弗斯背负的巨石,随时会再一次从山顶落下,反抗者也依然在承担着巨石的重负,但每一次他们都竭尽全力把石块打得粉碎。在这些反抗者身上,涌动着经过痛苦与勇气磨砺的强劲生命力。他们拒绝承认“存在即合理”,就像加缪日后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背负着我们的苦役、罪行与创伤。然而我们的任务并非把它们释放到世界上,而是在我们身上以及其他人那里与它们斗争。”从承担巨石到打碎巨石,加缪以此完成了“荒诞系列”向“反抗系列”的演进。他在《鼠疫》中写道:“出于良心的准则,他(里厄)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一方,希望与人类、与他的同胞重聚,在他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唯一确信的事物中重聚,也就是爱、苦难与流亡。于是没有任何一份同胞的焦虑他未曾与之分担,也没有任何一种处境不是他自己的处境。”世界从本质上是荒诞的,但不止于荒诞。认识荒诞,反抗荒诞,在反抗中不断创造生命的意义,互相激励与扶持,团结和分担,正是这一切使得反抗者的行为拥有了切实的价值,这已然堪称“决定性的进步”。
本文节选自读客版《鼠疫》导读,原文将近两万字,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经出版方读客授权刊发。
撰文 张博
摘编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