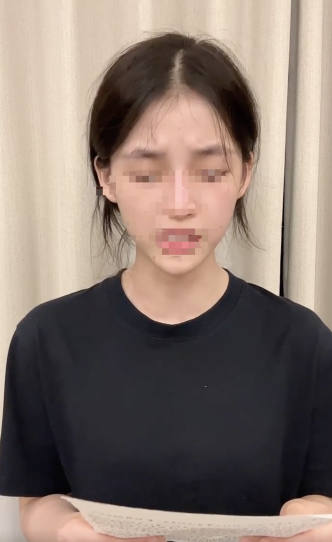清末诗人易顺鼎在《天桥曲》中,写道:“垂柳腰肢全似女,斜阳颜色好于花。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
天桥曾经和西单、鼓楼、东四一样,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元明时期天桥就已经出现了市场,到清代末期已经发展得繁荣异常。来天桥,不仅可以看戏逛茶馆,更有数不尽的小吃摊,最使天桥与众不同的,还要数应有尽有的民间艺术表演。来天桥,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如今的天桥虽不复当年,但广场上仍有天桥“八大怪”的塑像。所谓天桥“八大怪”,指的是活跃在天桥地带、技艺超群的八位民间艺人。京味儿文学作家刘一达曾在八十年代到天桥采访过几位老艺人,梳理了三代天桥“八大怪”的历史。
本文选自《典故北京》,较原文有删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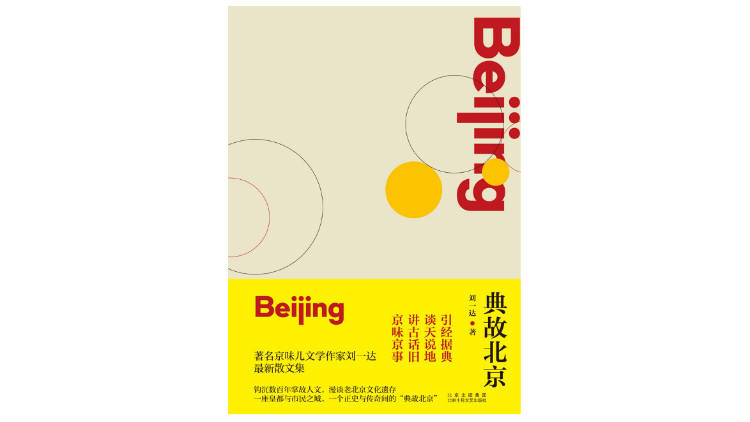
《典故北京》,刘一达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原文作者丨刘一达
摘编丨镜陶
“五花八门”是哪“五花”,哪“八门”?
老北京人聊到天桥的时候,一定会说:“那地方真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五花八门”,五岁小孩儿也会知道这是一句成语。但什么叫“五花八门”?哪“五花”,哪“八门”?深问您一句,您就不见得知道了。
有人解释“五花八门”,是指中国古代打仗的阵势。古人打仗讲究排兵布阵,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行阵”和“八门阵”,“五花八门”就是指这两个阵势,因为它们变化多端,让人眼花缭乱,所以这个成语有目不暇接的意思。
可这个成语既然是典出“五行阵”和“八门阵”,为什么不叫“五行八门”,却叫“五花八门”呢?显然,这种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其实,“五花八门”是过去的江湖的隐语,“五花”和“八门”都是有所指的。
“五花”,喻指五种花,而且这五种花都是喻人的。
它们是:“金菊花”,喻指卖茶的女子;“木棉花”,喻指走街串巷为人看病的游医,即郎中;“水仙花”,喻指妓女;“火棘花”,喻指杂耍演员;“土中花”,喻指挑夫。
“八门”,指的是过去江湖上卖艺耍手艺的八种人,简单说就是“巾皮彩挂,平团调柳”。
具体讲:“巾”,指的是看相算命的;“皮”,指的是卖中草药的;“彩”,指的是变戏法的;“挂”,指的是江湖卖艺的;“平”,指的是说书弹唱的;“团”,指的是街头卖唱的;“调”,指的是搭棚扎纸的;“柳”,指的是高台唱戏的。
这“五花八门”,您在老北京天桥都能找到。不能说天桥这地界,出产“五花八门”的这些江湖艺人;只能说天桥特有的“气场”,适合“五花八门”的这些江湖艺人生存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天桥在老北京人眼里是块“杂巴地”。江湖上的许多好玩儿的有趣的,您在这儿能见到。江湖上那些坑蒙拐骗,见不得人的阴暗事儿,您在这儿也能碰到。
当然,天桥最诱惑人的是杂耍、曲艺等民间的表演艺术,它也被视为老北京曲艺和杂技的发源地,比如相声就是在天桥产生的,还有一些曲艺的曲种、杂技的表演是在天桥唱出来演出来的,包括代表北京的剧种评剧。

北平沦陷时期,民间艺人金业勤在天桥卖艺。
第一代天桥“八大怪”
在天桥各种民间表演艺术中,最有名的就是“八大怪”了。这“八大怪”,是八位以“怪”著称的艺人,跟“八门”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艺人能跟这个“怪”字沾边,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其身手肯定不凡,而且要有与众不同的绝活儿。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多次到天桥地区采访。当时天桥地区的许多老胡同和平房还没拆,老天桥演艺场子的遗迹尚存,一些天桥的老艺人还在。在这里的街巷漫步,还能感觉到老天桥的古韵。
我先后采访了“大狗熊”“飞飞飞”“虫子杨”“大刀张”张宝忠的儿子张少杰、“摔跤满”满宝珍、玩车技的“小老黑儿”等老天桥有名的艺人。
双簧表演艺术家孙宝才,绰号“大狗熊”,当时一些文章说他是天桥的“八大怪”之一。我采访他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老爷子是在北京曲艺团退的休,土生土长的“天桥人”。他笑着对我说:“我可够不上‘八大怪’。当年天桥的‘八大怪’在京城赫赫有名,家喻户晓,说他们‘怪’,名不虚传。他们的玩意儿真够得上这个‘怪’字。”
“八大怪”,人怪,玩意儿怪,对他们的说法也“怪”。
“八大怪”究竟都是谁?在天桥的地面儿上,居然也说法不一。记得当时我问了许多人,这个告诉我“八大怪”都有谁,那个告诉我“八大怪”是谁,十个人十个说法,最后把他们告诉我的“怪”放到一起梳理,竟然弄出二十多个“怪”来。
到底谁是“八大怪”呢?后来我查了许多老北京有关天桥的史料,发现原来这“八大怪”是有“时间段”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八大怪”。
“八大怪”是天桥艺人们比较公认的“怪人”。这些“怪人”出现在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这个时期,是天桥民间艺人的初起阶段,被人们评为“八大怪”的算是第一拨。
这拨“八大怪”的第一“怪”,是唱太平歌词、说相声的朱绍文,他的艺名叫“穷不怕”,祖籍浙江绍兴,是汉军旗人。

“穷不怕”
朱绍文生于1829年,死于1904年,活了七十五岁。他从小学的是京剧,唱架子花脸,后来标新立异,改唱太平歌词,并与说相声的“孙丑子”结拜为把兄弟。
在天桥表演,行话叫“撂地”,即在地面儿圈出一块场地,演员在“地上”表演,演完一段,向观众收钱,所以又叫“平地抠饼”。要想让观众掏钱,您必须得有真功夫。
朱绍文会的玩意儿很多,他除了即兴演唱太平歌词,还擅长用白沙子在地上撒字,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撒的一副对联:“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字翰林书。”
这副对联正着念,反着念,音是一样的。写这些是为了“粘圆子”,江湖术语招人的意思。白沙撒字,堪称天桥一“怪”。
朱绍文还会打竹板,他手里的竹板上刻着两句话:“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穷不怕”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贫有本”,一个叫“穷有根”,有时三人一块说相声。他们编的相声针砭时弊,嘲讽陋习,一时传为佳话。
1872年出版的《都门汇纂》里,有一首说他的《竹枝词》:“白沙撒字作生涯,欲索钱财谑语发,弟子更呼‘贫有本’,师徒名色也堪夸。”
相声这种表演形式,在朱绍文之前,已经在天桥出现,但是朱绍文有文化,他改编了许多民间笑话,并且采用说、学、逗、唱的形式,使相声这种民间表演更加完善。
朱绍文创作了许多相声作品,如《字象》《黄鹤楼》《庄公打马》《八大改行》等,已成为经典作品,至今仍被相声演员表演。
第二“怪”是滑稽演员“醋溺高”。“醋溺高”是他的外号,什么意思呢?至今无解。江湖上只知道这个人姓高,叫什么名不知道。
此人整天蓬头垢面,留着脏兮兮的大胡子,身穿油脂麻花的布袍,一脸滑稽相,擅长模仿各种人物,说学逗唱,无所不能。
《朝市丛载》一书对他的描写是:“一脸黑泥连鬓毛,手拈草珠旧纱袍。骂人都作寻常事,得意人呼醋溺高。”
第三“怪”是演滑稽的“韩麻子”。此人也没留下名字,人们只知道他姓韩。
他怪在长的模样上,冬瓜脑袋,紫黑的脸,眉目怪诞,奇丑无比,一脸麻子,前额还有几道梅花纹。
他的这副尊容本身就惹人发笑,再加上他擅长说、学、逗、唱,所以,在天桥,不用拉场子,拎着大鸟笼子,往那儿一站,便会招来许多看客。
第四“怪”是敲盆唱曲的“盆儿秃子”。人们也不知其姓名,只知道他的绰号。
所谓的“盆儿”,是他在天桥表演,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口径一尺长的瓦盆,用筷子能敲出悦耳的声响,一边敲,一边哼唱自编的太平歌词,经常“现挂”抓哏,让人捧腹。
《天桥杂咏》里形容他:“曾见当年盆秃子,盆儿敲得韵铮铮。而今市井夸新调,岂识秦人善此声。”
第五“怪”是玩杠子的“田瘸子”。人们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走道一瘸一拐,但在杠子上却身手不凡,既能寒鸦浮水,又能鹞子翻身,最绝的是他能以两个手指支撑,在杠子上倒立“拿大顶”,让人百看不厌。
《朝市丛载》中对他赞誉道:“瘸腿何曾是废人,练成杠子更通神。寒鸦浮水头朝下,遍身功夫在上身。”
第六“怪”是表演化装相声的“孙丑子”,人们也只知道他的外号,不知他名字。他是“穷不怕”的师兄弟,以说相声谋生。长相丑,又常常穿着奇怪的装束,有时甚至穿着出殡的丧袍,披麻戴孝,手里拿着招魂幡,做出各种怪相,来博取人们的开心一笑。
《天桥杂咏》一书对他的评价是:“为谋生计戴麻冠,行哭爸爸又呼冤。莫道国人多忌讳,也知除假使真钱。”显然对他的这种自轻自贱、低级下作的表演是嘲讽的。
第七“怪”是表演吹鼻嗡子的“打麻铁壶的”,他连姓名都没留下来,人们只记住了他演的玩意儿了。
“吹鼻嗡子”就是用两个特制的小竹管儿插到鼻孔里,然后使劲用鼻音通过竹管发出有韵律的音响。随着音响,他还要哼唱自编的小调。与此同时,他的腰上还挎着一个破铁壶,一边唱着,一边敲打着这铁壶,十分风趣,逗人发笑。
《天桥杂咏》里对他的描写是:“麻铁壶敲韵调扬,亦能随手协宫商。当时牛鬼蛇神样,看到而今转觉强。”
第八“怪”是耍石头的“常傻子”,人们只知道他姓常,名字没有留下来。外号“傻”,其实他并不傻。在天桥卖艺时,常带着他的弟弟,哥儿俩一块耍石头。

常傻子
他耍石头兼卖丸药,即所谓“大力丸”。“撂地”时,放着大大小小的一堆石头,旁边是铁匣子,里面装着“大力丸”。
表演时,手里拿着一块青石,面对一块大石头,嘴里振振有词,然后屏气凝神,大喊一声照着那石头砸下去,顿时石头粉碎。
这时,他对现场的观众说,这是吃了“大力丸”之后才有的力气,撺掇大伙儿买药。这大概是最早的商品推销术。
《天桥杂咏》对他的描述是:“猛向石头哈一声,抡开双臂定双睛。石头撤去石头垫,肉绽皮开也不成。仙家煮石事荒唐,常傻而今可做粮。顽石且能迎手碎,何须更觅点金方。”
以上的第一拨天桥“八大怪”,有三个特点:
一是除朱绍文之外,其他七“怪”都有姓,却没留下名字,可见他们几乎没有文化,社会地位比较低。
二是他们的“怪”,是因为长得丑。您瞧吧,不是麻子、秃子、瘸子,就是傻子、丑子,没一个长得顺溜的。
三是他们的表演比较简单,有的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只是靠长相古怪,或穿着奇特,做“怪”样,出洋相来博取观众的欢心。
第一拨的“八大怪”,多少有拿这些人“开涮”和嘲弄的意味。当然他们的表演,除了“穷不怕”以外,也没有什么“艺”可以传承的。
第二拨天桥“八大怪”
在清末民初,20世纪一二十年代,即辛亥革命前后,天桥又出现了一批“怪人”,被人称为第二拨“八大怪”。他们是:
第一“怪”是“老云里飞”。他的真名叫白庆林,堂号“庆有轩”。他最早是梨园行的武生演员,在天桥卖艺除了唱两口,也靠打把式翻跟头招揽观众。
他“撂地”的场子,用白灰写着“云里飞,壁里蹦,雨来散,风来乱”。他的跟头翻得高,也翻得远,给人以云中翻滚的感觉,“云里飞”名不虚传。
第二“怪”是用鼻哨吹戏的“花狗熊”,只留下外号,没留下真实姓名,他的功夫是用两根竹管插进鼻孔,能吹出许多戏曲,还有各种鸟兽的声音,边吹边唱,插科打诨,逗人发笑。
第三“怪”是口技演员“百鸟张”,他的真名叫张昆山,老北京的许多报章都介绍过他,其口技表演惟妙惟肖,自称“凡是能飞的一概能学”。“百鸟张”的口技当年在京城家喻户晓。《都市丛载》说他:“学来禽语韵低昂,都下传呼‘百鸟张’。最是柳荫酣醉后,一声婉转听莺簧。”
第四“怪”是耍活蛤蟆的,只留下了玩意儿,没留下姓名。因这个演员年过花甲,演出时呼蛤蟆是学生,一招呼学生,蛤蟆便自己爬过来,所以人们又叫他“教书老先生”。其实他并没文化,靠玩蛤蟆玩出了名儿。
第五“怪”是耍金钟卖唱的,也没留下姓名,人们只记住了他的玩意儿。所谓“金钟”,是锃光瓦亮的一个铜筒子,亮如明镜,演员拿出各种图片,照在铜筒子上,幻化出不同影像,演员一边摆弄图片,一边唱小曲,非常滑稽。
第六“怪”是耍中幡的“王小辫”,这在当年天桥是非常有名的表演项目。中幡是用长三丈多的竹竿,挑起顶部的伞盖,伞布两边配有小旗和串铃,整个中幡有几十斤重。

“王小辫”
“王小辫”托在手上,顶在肩上、头部、胸前后背,能耍出一套完整的动作,有“霸王举鼎”“朝天一炷香”等名堂。“王小辫”在耍中幡的同时,还带着徒弟现场摔跤表演,每天都能吸引许多观众。
后来,他的徒弟宝善林“宝三”,继承了他的中幡表演绝活儿,现在,天桥的中幡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七“怪”是练铁锤的志真和尚。此人的一绝是,手拿几十斤重的铁锤,一边大喊,一边朝自己的胸部猛击,却无任何疼痛之感。练完之后,他便兜售自己炮制的“切糕丸”,声称吃了这种药丸,不但能治饿,还能抗击打。
《江湖丛画》对他的这种“怪举”写道:“卖打夸张药力真,街头叫喊为惊人。频敲左肋砰砰响,也是千锤百炼身。少林肯传授轻抛,两个铜元卖一包。不信当场来试验,小僧能挺铁锤敲。”
第八“怪”是耍狗熊顶碗的“程傻子”。此人在老天桥非常有名,绝活儿是头上能顶十三个花碗,而且顶着碗能做许多高难度动作,花样让人看了目不暇接。
除了这个绝活儿,他还会耍狗熊,是天桥艺人的一个招牌。《江湖丛画》中对他描写道:“程傻登场不耍熊,十三宝塔耍尤工。要知饭碗熊牢固,第一全凭顶上功。”
第三代天桥“八大怪”
民国以后到1949年北平解放,天桥的演艺场子又出现了一些奇人,人们列出八位来,把他们看作是第三拨“八大怪”。他们是:
第一“怪”是表演滑稽和相声的“小云里飞”,他的大号叫白宝山,是老“云里飞”的儿子。因为他戏曲武功出众,折跟头打把式让人眼花缭乱,人送外号“草上飞”“壁里蹦”。
“小云里飞”从小跟父亲在天桥“撂地”,继承了父亲的功夫,又有所创新,每次演出,带着儿子白全福和弟子,每个人扮演不同角色,说学逗唱,插科打诨,逗人发笑。
相声的“柳活儿”到他这儿日趋成熟,他留下了许多“柳活儿”的经典,如《炸酱面》《空城计》等,相声名家侯宝林、郭全宝等都跟他学过艺。
第二“怪”是拉洋片的“大金牙”,他的本名叫焦德池,因为嘴里镶着金牙而得此绰号。拉洋片是他首唱,同时他还研究出一套配合照片的唱段。

“大金牙”
后来,他的儿子继承了拉洋片的演唱技巧,现在,拉洋片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怪”是骂大街的“大兵黄”,此人大号黄才贵,早年在军阀部队当过兵,也负过伤,练就了他身上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
他在天桥主要是靠卖药糖谋生,为了招人,他身上穿着黄马褂、紫缎子长袍,手持文明棍,对官场和民间看着不顺眼的事儿,便扯着嗓子叫骂。他骂人骂事,鞭辟入里,酣畅淋漓,都是老百姓想说不敢说的,所以观众听了都觉得解气。
虽然他多次被巡警抓走,但他的“兵痞”劲头儿,谁也奈何不了。抓了放,放了抓,最后索性放任自流了。“大兵黄”骂大街,当年在天桥绝对是一“景”,当然也是一“怪”了。
第四“怪”是表演耍牛骨数来宝的“曹麻子”,他的本名叫曹德奎。他从小跟“黑泥鳅李”学艺,在天桥“撂地”时,带两个徒弟,化上装,手里拿着“合扇”,这种响器俗称牛胯骨,上面有十三个小铃铛,所以又叫“十三太保”,两个徒弟也化上装,手里打着快板。
表演时,“曹麻子”常常现抓词儿,内容主要是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阴暗的。这些段子被后人整理,现在还有演员表演,例如《骂摩登》《打天坛》《变法》《拆城墙》等。
第五“怪”是说对口相声的焦德海。他是徐有禄的徒弟,相声“八德”之一,给他捧哏的是刘德智,他说的相声亦庄亦谐,模拟人物惟妙惟肖,拿手的名段《交地租》《羊上树》《粥挑子》等,令人捧腹。
不过,把他列入“八怪”有些牵强,因为跟那些“怪”人相比,他的幽默还是比较“文”的。他的徒弟有单口名家张寿臣,以及白宝亭、于俊波等。
第六“怪”是练气功和摔跤的沈三。沈三是天桥的名家,当年他的气功绝活儿“胸前开石”“双风贯耳”等,现在仍被人津津乐道。
所幸这些绝活儿被后人传承,现在还有人能表演。沈三的摔跤也很有名,他的徒弟后来有的成为全国中国式摔跤冠军。
第七“怪”是蹭油的“催巴儿”。他的本名叫周绍棠,“催巴儿”是带有贬义的老北京话,即“祟催”,给人打下手之意。
他不是艺人,是卖野药的,主要卖能去油污的药剂和治皮癣的药。跟一般摆摊儿设棚卖药的不同,他边走边吆喝,有时还故意在人衣服上蹭点油污,然后用他的药剂当场擦拭。
逛天桥的都知道天桥有这么一号,但他在人群中到处游窜,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他蹭一下,所以在老天桥他成了“怪”人。
第八“怪”是表演赛活驴的关德俊。驴是用黑布精心制作的,驴头做得跟真驴相仿,穿在身上,像“活”驴一样,舞台上有许多道具,表演时的一些高难度动作,让人提心吊胆,但他却从容不迫。“赛活驴”的表演作为老天桥的民间艺术,已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有演出。
天桥的“八大怪”仅仅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其实,老天桥卖艺的知名艺人和“怪人”绝对不止这些,比如史料记载过的“架黄瓜”“张狗子”“气功断石傻子”,等等。
天桥三个不同时期的“八大怪”,还是很有代表性的,通过这些“怪”,可以看出老天桥的特点,您要想在天桥的地面儿上刨食,想要出人头地,不在艺术上有绝活儿,就得在“怪”上做文章。
比如那位靠骂大街出名的“大兵黄”,“怪”到让人称奇了,您也就出名了。由此说来,老天桥本来就是一个很怪的地方。
原文作者 | 刘一达
摘编 | 镜陶
编辑 | 王青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