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本能的思考,也有自我表达的手段策略;但这些好品质却被掩盖在他混进自己剧作中的垃圾底下。
——法国人对莎士比亚可考最早的评论,17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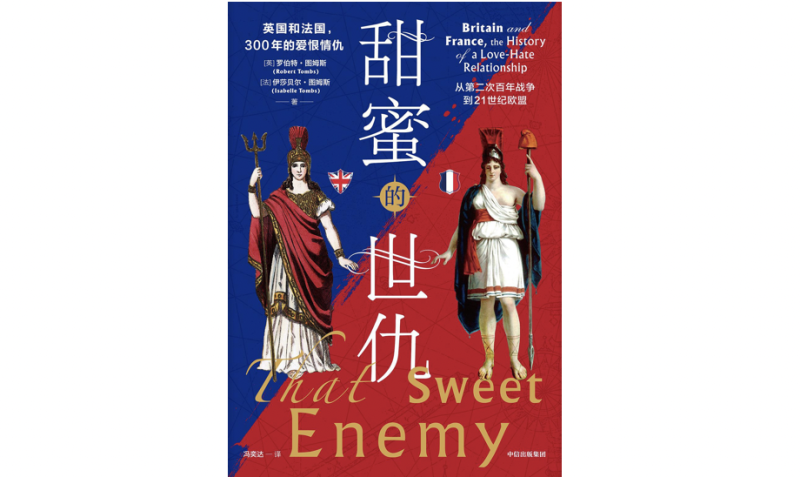
《甜蜜的世仇:英国和法国,300年的爱恨情仇》,[英]罗伯特·图姆斯 [法]伊莎贝尔·图姆斯 著,冯奕达 译,新思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版。
莎士比亚是法国人对英格兰
文化态度的风向标
莎士比亚向来是法国人对英格兰文化态度的风向标。自从伏尔泰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哲学通信》(1734)中引介他以来,他就成了众人眼中英格兰神魂之精髓——“有力而多产的天才,兼具自然与崇高,没有一丝文雅,也没有一点对规矩的认知……假使像马尔利宫花园中的灌木一般被塑形、修剪,英格兰创作之神魂便会死去”。
打从一开始,人们便把这英格兰“神魂”明确视为法兰西精神的对立面。因此,评判莎士比亚,也就等于评判法国文化。于是乎,伏尔泰一面夸奖莎士比亚的质朴之美,一面强调其质朴之罪:强有力但缺乏礼法;原创但不老练;深刻但不一致;崇高的诗意瞬间被卑鄙的下层角色、粗野嘈杂的举动、无端的暴力与一贯的傻气败坏。伏尔泰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功,令不良习性根植于英格兰舞台,从而伤害了舞台;此外,英格兰语言恐怕正在衰微。

《哈姆雷特》(2015)剧照,英国国家剧院现场。
伏尔泰当然认为自己根据莎翁主题所写的剧本——例如颇受欢迎的《恺撒之死》(Mort de César,1733),以及受《奥赛罗》(Othello)启发的《扎伊尔》(Zaïre,1732)——比其原作更成功,足以凭借适度注入莎翁活力的做法,让法国戏剧界恢复活力。他在1750年写道:“我们用太多的台词,就好比你们用太多的动作,情况确实如此;或许,至臻完美的艺术,是混合了法兰西的品味与英格兰的精力。”他始终认为法国文学更为优越,因此喜爱爱迪生甚于莎士比亚,因为爱迪生下笔就像法国人,优雅、雕琢、精准。
伏尔泰的看法不只法国人接受,在英格兰也颇有人认同,这证明法国古典风格(包括他自己的戏,其中有16部在伦敦制作)的威望仍然存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海峡两岸都遭受审查、修正,连捍卫莎翁不遗余力的塞缪尔·约翰逊与戴维·加里克也参与过。他的词被改得更有诗意,剧情被改得更好懂,结局也被改得更开心。
伏尔泰引发的莎翁风潮,很快就超越他屈尊俯就的赞赏。下一代的作家与启蒙哲人之所以钦佩莎士比亚,原因正是他不理睬古典惯例:“诗意之神魂有其独立精神,其挥洒自如、不受众多规矩局限,令人羡慕。”18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热爱法兰西但爱国的加里克(他是胡格诺信徒之子)在巴黎的沙龙搬演莎士比亚选粹,同时将莎士比亚当成民族诗人、英格兰戏剧之卫士,重新引介回英国的舞台。
赞扬莎士比亚,便会冷落高乃依(Corneille)与拉辛(Racine) 的古典戏剧传统,而伏尔泰本人正是两人在当时的头号支持者。他决定挫挫这位已死对手的锐气。伏尔泰的敌意起自 18 世纪 40 年代,当时他将《哈姆雷特》(Hamlet)描述为“下流野蛮的东西,连法兰西或意大利最底层的民众都无法容忍”,而虚荣心与政治目的加深了他的敌意。但底下作祟的不止虚荣心。法国古典戏剧是哲思的(凸显道德两难),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是心理的(探究角色的发展,这正是加里克的“哑剧”带来的冲击——用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演戏,而非单纯朗诵韵文)。

《哈姆雷特》(2015)剧照,英国国家剧院现场。
法国戏剧的基础,在于以诗意的方式描述舞台外的事件,而莎翁戏剧的基础就是在其舞台表现(例如打斗、杀人等让人不愉快的场景)。前者凝聚而有序(严守时间、空间与行动的统一),后者散漫、繁复,甚至前后不连贯。前者道德,而且多半乐观,后者不只不道德,而且经常悲观。前者对受教育的精英有吸引力,后者则吸引普罗大众。在伏尔泰来看,前者就是更高级的艺术形式,由更超前的文明所创造;后者无论多么有力,都是幼稚而粗糙的: “写一部好戏,当然比在舞台上搬演谋杀、绞刑、女巫与鬼魂来得更难。”
伏尔泰好比高傲的音乐评论人,赏个脸承认披头士的歌也有优点,等到人们开始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acartney)比舒伯特更厉害,就觉得天崩地裂。只是这一回,被比下去的是伏尔泰。他哀号说:“我原想加入多些动作,让剧场界活络些,谁知现在一切都是动作跟哑剧……再见了,精致的韵文;再见了,真挚的情感;再见了,一切。”他对朋友忏悔道:“这起灾难中最惨的是,当初第一个提到莎士比亚此君的人是我,是我把自己在他庞大粪堆中找到的几颗珍珠拿给法国人看的。”
法国文坛在“创造力”
与“品味”之争中分裂
七年战争创造了恐英的氛围,英国的文化影响力似乎正挑战法国的优势地位。1761年,伏尔泰(宣称要为故土而战)发表《告欧洲各民族书》(Appeal to All the Nations of Europe)。这是他对英格兰文化下的战书。
莎士比亚如今成了“乡下小丑”、“野蛮的江湖骗子”和“醉酒的蛮子”。他给《哈姆雷特》剧情做了番假装严肃的摘要,转述其中的若干台词,使之听起来荒谬、粗野而愚蠢。他用“英格兰社会缺乏鉴别力”来解释莎翁的成就,说对于英格兰的“搬运工、船员、车夫、小二、屠夫和店员”来说,舞台上的暴力、喜剧和奇风异俗就是其娱乐, 而这些人制定的公共标准“让欧洲各地品味高雅的人士感到憎恶”。
加里克则押上了更多赌注,在 1769年举办了爱国意味浓厚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等到皮埃尔·勒·图纳尔(Pierre Le Tourneur)在177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译成 20 册),同样的活动又举办了一次。图纳尔版的莎士比亚剧作是用来阅读的,而非表演的,目标在于忠于原著,忠实程度远甚于剧场惯例所能容许的程度。尽管忠于原著,“卑鄙庸俗”的用词还是要改得文雅。《奥赛罗》里的“黑公羊……跟你的白母羊交欢”变成“黑秃鹰”和“年幼的白鸽”。单纯的俗语也改得像诗兴大发:狗变成“秃鹫”,蟋蟀变成“地里的昆虫”,如此这般。
勒·图纳尔的版本成就惊人,连王室成员与重要政治人物(包括恐英的舒瓦瑟尔公爵)都成了订户——这是莎士比亚与英格兰文化声望的有力象征,两国当时甚至处在战争边缘。勒·图纳尔在献给国王的序言中,宣称“从来没有任何天才人物能如此直指人心至深处”或创造出“这般自然的”角色。
伏尔泰勃然大怒,“这个粗鲁的傻瓜”居然高举莎士比亚为“地道悲剧的唯一典范……将拉辛与高乃依的冠冕重重踩在脚下”,借此侮辱法兰西。他给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去信,谴责莎士比亚伤风败俗的用语和“恶名昭彰之堕落”,若干内容“竟大胆违抗我们戏剧界的威仪”。信在1776 年 8 月由达朗贝尔在学院中宣读,出席的英国大使斯托蒙特勋爵(Lord Stormont)大为不悦,伊丽莎白·蒙塔古也在场,表情也很严峻。针对伏尔泰早先的抨击,她写了一篇踩中痛脚的反驳文章——《论莎士比亚之写作与天才——与希腊和法国剧作家比较》,而这只是从海峡对岸咆哮而来的众多反击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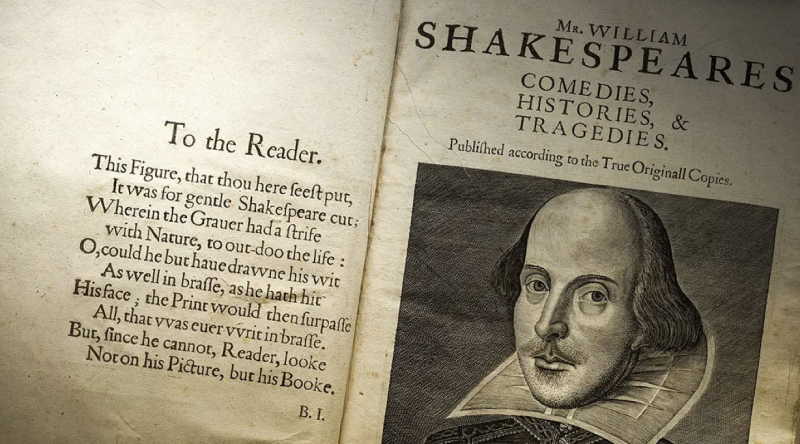
纪录片《莎翁遗嘱》(2012)剧照。
法国文坛在“创造力”与“品味”之争中分裂。借蒙塔古的话来说:“创造力,唯有强而有力的创造力(狂野自然之气势从根作用起!)才能创造出如此强烈、与众不同的美。”创造力赢了——但不是完全桀骜不驯。
莎士比亚的剧作也得被驯化,一如在英格兰的情况。让-弗朗索瓦·迪西(Jean-François Ducis)把莎翁改得让法国观众“能够承受”,删去了不雅观的动作与不舒服的剧情,还加入了芭蕾舞(但他英文不好,是从译本改的)。他毫不忌讳的改写(以《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受欢迎)在18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1783年,《李尔王》(在迪西的修改后,这部戏以喜剧收场)在凡尔赛宫初演——法国与英国当时还在打仗,这简直不可思议。好戏还在后头:1793年9月,两国再度对垒,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正值高峰,而音乐剧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却成功在巴黎制作登台了。
本文选自《甜蜜的世仇:英国和法国,300年的爱恨情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罗伯特·图姆斯 [法]伊莎贝尔·图姆斯
摘编/何也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