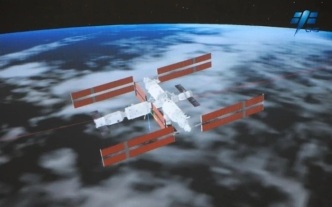去大理,有人为追寻苍山洱海的美景,也有人为体会风花雪月的浪漫,还有人为逃离焦虑内卷的城市……
2022年初,一群刚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来到大理古生村,这是一个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古村落,有如画的风景和成片的农田,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曾在这里取景。
和其他到大理的人们不同,学生们住在村民的小院中,跟着农民一起下地种田,翻找村民们的生活垃圾,分析他们的饮食结构,日复一日地进行水质和土壤监测,调查环境污染的来源,开展绿色种植技术的创新研究等。
他们之中,有人刚刚考上研究生,有人初次走出校园和实验室,有人第一次下地干活,初次干农活的他们,就像综艺节目《种地吧少年》一样。但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为了体验农耕生活,而是带着知识和技术,用他们自己的办法,一点点地改变着这里的乡村和农田。

云南农业大学研一学生杨静(右),和同学吉佳(左)在油菜地里进行作物长势调查。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洱海边上,农学生们正在春播
3月26日,早晨七点左右,23岁的王昕骑着电动三轮车,穿过弯弯曲曲的村道,一路驶向村外的农田。

王昕用电动车载着地膜等农资下地。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阳光在山巅上露出一缕晨曦时,王昕和她的同学们,正在艰难地尝试操作一台自动移栽机,把育好的油菜苗移栽到覆着黑色地膜的垄上。他们用口罩或面纱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穿着印有“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红色冲锋衣,这身打扮和当地村民几乎一模一样。
这是一块进行“周年油菜薹”种植的试验田,大约两亩多。王昕是这块地的负责人,平时由她带着几个工人照顾这块地,到了需要移栽油菜的农忙时节,同学们都会一起来帮忙。

科技小院的学生们和当地村民一起下地干活。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王昕是中国农业大学研二的学生,学水利工程的她,从没想过,研究生的生涯,从下地种油菜开始。2022年,学完专业课的王昕,被派驻到古生村的科技小院,和两位师兄一位师弟组成了水分管理小组中的一个小分队,负责一亩半蚕豆和两亩油菜薹的种植试验,这一次,她要在村里住一年左右,一直到毕业。
王昕负责的这块油菜薹地,已经收获过一次。新一茬的种植和上一次不同,一辆来自昆明理工大学的小型移栽机加入了他们的团队。移栽机只有180公斤重,一辆面包车就可以拉到地头,两个人就可以操作,一个人操作机器,一个人负责装填油菜苗。

移栽机的研发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和团队老师,带着科技小院的学生们,使用新设备移栽油菜。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移栽机的研发团队、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刘建雄团队,在现场指导学生们调式装备,尝试不同的办法。时间一点点过去,他们的配合从生疏变得默契,作业速度也越来越快。“比预想得更好。”王昕说。
这块油菜地里,还有很多新的技术同时在试验,包括可降解的地膜覆盖、膜下滴灌等,都是为大理干旱的小春季节设计的。地膜覆盖可以有效保墒保温、控制杂草,膜下滴灌则是将滴灌的管道安置在地膜下面,保证水分得到最大化利用。
进村下地,大学生们的新生活
科技小院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于2009年创立的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助农新模式。让老师、学生及合作团队的科研人员住在农村,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十五年来,科技小院已经成立了一千多个,遍布全国各地。
王昕是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的一员,古生村的科技小院建立时间很短,但规模不小。这源于古生村特殊的环境,古生村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山海之间,有一片相对平坦的土地。这里农业发达,村庄人口众多,是探索生态保护与农业绿色高值发展的绝佳场地。因此,从2021年,第一批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到来之后,这里吸引了很多涉农高校、科研机构的目光。一年多来,他们在村里已经建设了8个科技小院,常年有100多位学生、数十位教师在这里驻村,和农民一起生活、耕作,同时进行许多不同的科研项目。
王昕所在的水分管理小组,负责三十多亩油菜试验地的水肥一体化管理,与油菜组、蚕豆组等协同开展十多个不同的科学实验,共同为古生村及洱海周边的乡村,探寻既兼顾生态保护又能实现节水节肥、高效高值的农业种植模式。小组中的学生,大都和王昕一样,完成了专业课的学习就被派驻村里,一直到毕业。

傍晚收工前,王昕(左)和师弟臧胤霖(右)检查滴灌设备。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同在油菜组的杨静,几乎是和科技小院一同进入古生村的,来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她是云南大学农学院的研二学生,学的是园艺,来古生村之前,在学校里过着宿舍、课堂、实验室三点一线的生活,土地和种植,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学生,只有极少部分有过种地的经验。中国农业大学的研一学生任衍齐,小时候曾跟着父亲在山东老家种地,考上研究生后,又到了云南大理种地。任衍齐的父亲曾经问他,为啥考上研究生了还要种地,他告诉父亲,现在种地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靠经验、靠人力,现在靠科技,靠智慧。
学生意气,种地比想象中更难
从没下过地的农学生们,进村之后,一开始就要独立负责一块地的耕种管收,尽管在课堂和书本上已经学过很多知识,但初次实践,困难仍远超想象。
学生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并不是怎么种好一块地,而是怎么把农资运到地里。从村里到最远的地,大约一公里左右,多是笔直的田间路。尽管如此,动辄上百斤的农资,从村里搬到地里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在村里,农民们普遍使用电动三轮车,可以拉农资、农具,也可以拉收获的粮食和蔬菜。在经历肩扛手抬的艰辛之后,小院的师生们向农民学习,为每一个小组配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这成了他们的第一件“农具”。所有入驻科技小院的学生,都要先学会开三轮车,包括王昕这种第一次下地的女生。
“学开三轮是必备的技能,也是驻村后的第一件事情,一般都是先来的师兄师姐带我们,先会的带动后会的。三轮车学起来很快,但效果各有不同,有人很快就熟练了,有人很长时间还是不太敢开。”任衍齐说。
每天早晨七点左右,小院的学生们开着三轮车,一路穿过街巷,开出村子,在田间会合,又散入到一块块不同的地里。直到太阳落山,又开着车回来。
第一次下地的学生们,面对完全陌生的土地,唯一依靠的是课堂上学来的知识,但照着课本干,很可能会被农民嘲笑。

几位科技小院的同学在路边等待油菜苗的到来。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杨静和她的同学们,曾经带着尺子和称去地头,仔细划分每一块地,严格称量种子和肥料,帮助他们的农民笑他们,“你们是要造原子弹吗?这么精确。”
每一个学生,都要和农民学习怎么种地,怎么观察庄稼,什么时候需要追肥、什么时候需要浇水,“我们会提前做计划,按照不同作物的生长规律,制定播种、施肥、浇水的时间点。但是农民们不需要,他们总是能够提前提醒我们,然后我们发现他们每一次都是准确的。”任衍齐说。
种地是一门综合的技能,肥料、水、种子、土壤、农药等所有的领域都要了解,而在学校,他们往往只是学习一门专业。王昕是学习水利的、杨静是学习园艺的,但在地里,滴灌带损坏漏水,也要他们自己修,他们使用的水肥一体的滴灌设备,如果施肥罐的盖子没有拧紧,很容易崩开。杨静说,每个学生都被水管里的水肥喷过,有人喷到过眼睛,还有人喷进嘴里。
书中知识,也在改变着农民
农民改变了大学生们对土地和耕作的想象,大学生们,也在改变着农民千百年来耕作的习惯和方法。
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为古生村的土地设计了很多新的种植模式,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技术。2022年5月,小院水稻组的师生们在地里种了水稻。但他们发现,插秧后原本七八天就有变化的水稻,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生长的动静。油菜也是如此,不管是直播的种子,还是移栽的油菜苗,长势都很差。拔出来一看,根系非常弱小,几乎没有插进土壤中。
古生村位于海拔一千九百多米的高原上,这里春季长时间干旱,且早晚温度很低,不利于水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采用的覆膜、膜下滴灌的技术,用可降解的地膜保墒保湿,以保障春季作物的生长。
3月下旬,油菜种植之前,王昕带着工人们在地里起垄,在垄上铺设滴灌带,然后再铺上地膜,滴灌可以精准地浇灌作物的根部,提高水的利用率。滴灌带上覆膜,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和温度,还可以早期控草,减少锄草的工作,等到油菜长起来,草也就不长了。

科技小院的学生们使用新的移栽机移栽油菜。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南方多丘陵山地,机械化比平原更难,古生村周边的农田,尽管相对平坦,但布满了水泥浇灌的灌溉渠道,纵横交错,大机器进不了地。由于缺乏适宜的农业机械,起垄、覆膜、移栽油菜等工作,都是王昕带着工人们一起干的。但今年,他们已经有了适合丘陵坡地的小型器械。
学生们的试验田,和农民们种植的土地相比,渐渐出现了明显的区别。杨静负责的三十亩油菜地中,被划分成了很多小块,有的用直播方式种植,有的移栽。站在地边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杨静地里的油菜长势远比农民种得更好。
事实上,由于气候、降水等环境影响,当地农民种植的油菜,更多用于观赏,几乎没有实际的收益。很多农民的油菜地同时种着野豌豆,但他们种的油菜更多是作为绿肥使用,直接翻到地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走出校园,接触完整的社会
14个小院中的一百多个学生,并不都是从事农业种植的,还有大量从事农村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工作的学生。
学习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刘璐和严钰,都是点线面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分析、总结科技小院的工作机制和模式,是科技小院中的“战略部门”。但对驻村的学生们来说,学会怎样和村民接触,为乡村提供社会服务是基本技能,也是科技小院的基本要求。
怎样才能和村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2022年夏天,喜欢摄影的刘璐想到了一个主意,为村里人拍照、拍视频,拉近他们和村民的距离,记录村民们的真实生活。

科技小院学生严钰在村里拍摄。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和相对单一的学校不同,乡村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村民们也有很多故事,缺少的只是发掘和记录这些故事的人。一位退伍老兵的家里,保留着成排的军功章;一位留守村庄的妇女,心里装着许多不足以为外人道的记忆;一个回村创业的青年,正在规划着他的未来。
而几乎从未接触过社会的学生们,如何融入乡村,如何真正获得农民的信任,是他们驻村后必须克服的难题。
村民们大多很腼腆,他们可以和这些住在村里的大学生们一起聊天,但面对镜头,还是会下意识地躲开。严钰原本准备了道具,想在村中心的大榕树下给村民们集中拍照、拍视频,但他发现,很难说服他们在公开的场所展示自己。为此,他们不得不带着道具、幕布等,一家家走进村民的院子里去拍摄。
“面对镜头时他们会害羞,会拒绝,但最后拍摄的时候,还是挺感动的。”刘璐说。
在村庄中,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从2009年至今,数百位研究生从科技小院走出,也留下了许多故事。一位从未种过菠萝的研究生,在广东一个村中,先向农民学习,又和农民一起重振村里的菠萝产业,那里被中国农大的师生们称为“菠萝的海”。另一位学生在山东常驻在枣林里的小院,两年写了10篇论文。
在古生村,研一的韩朔和他的同学们,也在尝试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习惯。在早期调研洱海周边农业面源污染的时候,他们发现,看似干净整洁的乡村,对环境和水域的污染,远比想象中高。比如高油高盐的饮食习惯,使得厨余垃圾随着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进入水域,进而污染洱海。

小院学生们在探讨面源污染检测的情况。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调查这些污染究竟有多少?是怎样的形成的?韩朔和小组的同学们,从每一家村民们的日常垃圾产生状况开始入手。起初,他们和村民商量,在村民吃完晚饭之后,带着称去称村民一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分量,还翻开他们的垃圾桶,调查其他垃圾的具体种类、分量等。同时,他们还要调查村里的垃圾箱,将垃圾分拣出来,归类、称重。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大部分时候都是用手去翻。最开始,韩朔他们和村民约定时间,请村民们在下午统一扔垃圾,他们定时去调查。但后来发现,下午翻完垃圾,晚饭就完全吃不下去了,“第一回翻垃圾的时候,当时只是感觉很臭,但在真的去翻了之后,有同学真吐了。”他们还要面对村民们异样的眼光,“研究生还研究垃圾吗?”
事实上,研究生们确实在研究垃圾。为了探明农村居民生活与污染的关系,学生们一方面长期入户记录饮食收集厨余垃圾,在对厨余垃圾的分析中,村民们不合理的饮食习惯逐渐展现,这些垃圾造成污染的路径也更加清晰。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检测和对厨余垃圾的分析过程中,学生们为村民制定了新的食谱,叮嘱村民按照食谱调整饮食结构、减少油盐用量。“看着同学们帮助他们改变饮食习惯,比想象中简单,但也比想象中漫长。”韩朔说,在看到大学生们翻垃圾、称垃圾之后,村民们开始认可他们的工作,也愿意按照他们建议的食谱去做饭。但是如果不监督,过一段时间后,还会恢复原样。
村民们有时候还会看到村里三十多个大学生和老师们集体出动的场景,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
因为要监测洱海的水质,寻找面源污染的来源,师生们要在数百个监测点定期采样检测。而下雨时形成的径流,可能会将农田中的氮磷、村里的生活垃圾带入水中。因此,只要下雨,就要出门采样,如果半夜下雨,就要半夜爬起来去采样。

几个科技小院的学生,在溪水进入洱海的入水口采样。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在遇到暴雨监测的时候,每一个监测点就要分三个时间段采集样品,暴雨前十五分钟、暴雨中期十五分钟、雨量小的十五分钟,每个时间段每次要采三份样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在雨中作业至少一个小时。野外的路不好走,尤其是夜里,打伞反而让取样更难。后来,他们统一买了雨衣,“几十个人穿着黑色雨衣往野外跑,很壮观。”韩朔说。
村民们说,大学生们都很厉害
在大理,古生村是一个“明星村”,村里的人们,对来来往往的“客人”早已司空见惯。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来了又走,并不能真正给村里带来多少改变,也几乎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起初,他们觉得,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也是如此,可能就是来“考察”一下,走个过场,很快就会离开。

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古生村。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但村民们没想到的是,科技小院的师生住在村里的时间,远比想象中要长得多。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最长的住了300多天。他们没有寒暑假,也没有周末,和村里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他们走街串巷,进入每一个村民的家里,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也尝试着给村里带来新的变化。面前的洱海,一点点变得清澈,村后的农田,不断有新的作物和技术出现,村里的收入,也正在增长着。
3月26日下午,王昕还在田里忙着移栽油菜,刘璐在村里漫步,寻找拍摄的新素材。而55岁的村民黑庆贤,正抱着孙子坐在自家宽敞的院子里,院子铺了水泥地,和其他人家种满鲜花的小院明显不同。这个院子被师生们改造成了一个停车场,可以为外来的游客提供停车服务,不计时间,一次十元,仅在今年春节,就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元的收入。黑庆贤身后的二层小楼里,工人们正在改造,在室内加装卫浴设备,以供来客人使用。自从科技小院进村之后,村里来的人明显比以往多了,尤其是常驻的师生们,给村民们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变化。

风吹过洱海旁的小村庄。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黑庆贤家院外不远处,就是村子的中心,一棵大榕树长在路中间的一座高台上,榕树对面是座古戏台,周边开着几家商店、小吃店等。这是村里最繁华的地方,被学生们称为村里的CBD。古生村9社村民何银军的烧烤店就开在这里,半年多前,何银军还是一位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随着村里汇聚的人越来越多,他也结束了打工生涯,开了一家烧烤店,收入不比打工差,却可以留在村里照顾家人。何银军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刘璐和严钰所在的小组,为他们拍摄照片和视频。
“大学生们确实很厉害,有知识,又能吃苦,和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何银军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